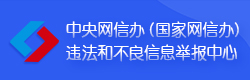画中之鹰无法品食夏日梅实
一
“天草先生,真的非常感谢。”
一个母亲向我鞠躬,随后带着她闹着要吃梅子的幼子离开我的诊所。
啊啊,已经七月了——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
其实我不大爱吃梅子。在极寒之时开花,酷热之时结出果子,这样一种生不逢时的植物,品尝之后的回忆往往只剩下酸涩。
但有一位我认为极可爱的女孩子很喜欢梅子,故而我也疑心它是有可爱之处的,只是我未曾发觉。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有想写点什么,以纪念从前的日子,却一直被各种事情耽搁。
但幸得吉原进那家伙推我一把,突然要我写一篇轻小说,要用一种水果为题,便使我不得不想起那位明媚的女孩子了。
虽然没能如何了解轻小说,但想来和小说是大体相似的,遂有此篇。
十年前,十二月。
我家附近都是些四方的建筑,被新下的雪映得更白,与世界上大多数城市一样,充斥着很没设计感的白色四角大楼。
“绘鹰,你说,未来如果我们真的分开了,你会这么回忆我呢,还是说会忘掉?”幸子伸出手在我面前挥挥,或许是要吸引注意力。
穿着加厚大衣的染井幸子狡黠地笑,抬头看我。
现在想来她还真是厉害,冬日着装竟不显得臃肿,米白大衣和咖啡色长围巾还隐隐有几分灵气。
“啊……”我多希望我能是一个更风趣的男人,可以巧妙回答这种送命的问题,可惜我并不是,只能发出不知所措的单音。
“是不会忘的,再说也不会分开哟,对吧?”幸子顶喜欢我尴尬的神色,刻意用大阪腔调述说她认定的事实。
幸子与我都在一栋公寓里长大,住着同样没什么设计感的屋子,十八年来虽没确认过关系,但大概也和婚后没什么两样。
天草家的小子和染井家的姑娘——历来是被同公寓的老人称道的,或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幸子展露的外向。
“嗯,当然不会,我们的关系比吉原进那家伙的牙坚固多了。”我立刻回答。
抱歉了进,现在只能用你来引开话题了。
怀着压根没有的抱歉,我再一次用进被梅子硌掉的牙齿开涮。
果不其然,幸子笑的花枝乱颤,直到呼吸不畅。
“绘鹰!你明知道我笑点低的。”她的额头冒出细汗,大笑果真是一项体力活。
“这不怪我,毕竟进就是这样好笑的人”
如同讲落语的搞笑角色,我想现实的就该是吉原进,仿佛供人玩笑是他们天生的才能,能让空气变得快活。
于是我再一次讲起进被梅子酸到双目紧闭的神态。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也认为进是因为眼睛闭的太紧而摔倒,以致丢掉了那颗门牙。
我说进就该再多吃些,好把丢失的门牙酸得生长出来。
但幸子毕竟是仁爱的,总会在话题渐渐危险的时候将我打断。
“真是的,绘鹰,明明梅子是极好的水果,也行正是你们不信任它,才常吃到酸的。”
“水果能感知到信任就很恐怖了吧!”
幸子凑到我的面前,脸颊如仓鼠般鼓起,抬起头认真与我对视,誓要为某种酸涩的果子正名。
“吉原君的牙和梅子才没有关系哩,明明是自己不小心。”
她生的极白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红,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使我不敢与她对视下去,于是匆匆别过头。
我仍没放弃为自己开脱:“但说成被梅子硌掉,不是更‘吉原进风格’嘛,而且更加简略。”
那年的冬天似乎一点也不冷,仅仅一层薄雪,有的梅枝已然开放。
正如幸子后来的宣言一致——“今天的绘鹰是在梅子之下的。”
她飞速跑开,在薄雪上印下脚印,又停下,回头等待着我去追赶。
我知晓她的用意,于是很快动身,也印下我的脚印。
“呼……呼……你跑的太快啦!”幸子很大口喘着气,性子活泼的她不擅运动,也许这就叫金无足赤。
当然,我并非容易妥协的男人,看着幸子的“惨状”,毫无慈悲的我双手抱胸:“现在谁不如一个水果呢?”
幸子抬起手,够到我的头:“乖哟乖哟,绘鹰你最好了。”
虽说对被当成小孩子这点有些不爽,但幸子终究是向我屈服了,倒也让人舒坦。
我们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接着一只微凉有些湿润的手向我伸来,我知道这是要我牵着她。
周末这种不上发条的日子里,幸子牵着我向那些毫无设计感的温馨建筑挪动,身后是细小的白梅,和薄薄的白雪。
二
对于学生而言,临近假期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十二月下旬就能迎来两周的寒假,这不能不让人兴奋,所以先生的传授只能从大脑中划走。
“进……进!”我伸手用铅笔戳了戳某个戴着墨镜上课的怪人。
“早上好啊,绘鹰。”进小声打着呵欠,向我问好。
原来他才睡醒么,用近乎参拜的虔诚眼神,我向他行了近十秒的注目礼。
“喂,你这是什么眼神,我的墨镜不就是这么用的吗?”
“说得好,墨镜怪人,其实你直接睡先生也不会管你的。”
随着我们毫无营养的闲谈,课上时间一晃而过。
几乎与铃声响起同一时间,进从椅子上蹦起来,打算一个人前往天台,用他的话说——骑士总是孤高的。
实际上,只是没有人愿意和这种怪人一起吃饭罢了。
不过这次我叫住他,要与他同去。
进将墨镜拉下一些,露出眼睛,上下扫视着我,拧身,挥手摆臂,做了一个自认帅气的动作,若没有把扣子崩开,就更加完美。
趁捡扣子的功夫,进开始他的讲话:“你终于被染井嫌弃,转而理解我的魅力了吗?可惜,在下喜欢女人。”
“如果你愿意,我会把这句话转述给大家。我和幸子就不劳挂念了,只是有事要和你分析。”
现在想来,与进分析事情,绝对是最大的问题。
“啧,无情的男人——去天台吧,面包分你一半。”
……
“所以你想和染井创造更多可纪念的回忆?”进摩挲着下巴,我坚信非同寻常的点子一定要他这样的怪人才能想出。
进徘徊几步,摘下墨镜,带着激情呐喊:“去〇〇吧!”
或是看见我渐渐阴沉的神色,进抹一把并不存在的汗,加速分析起来
“绘鹰你看——染井和你交往这么多年,你甚至没有与她确认关系,这种时刻才值得纪念啊!”
这时我居然对他有几分认可了,确实应该和幸子确认关系。
“所以你看,告白完就是要〇〇的。”进的神色愈发笃定,也许这就是白痴的特性。
“建议少玩点色情游戏。”
没有顾及某个白痴的抗议,我转身,径直走下天台,这家伙说的话,也只有一部分能听。
下午的国文和英语更无赘述的必要,同为归宅部的社员,我与幸子挺过这两节课,便是可以直接回家的。
我看见幸子在门口等着,于是跑过去。我的心里算不得平静,中午的想法还在盘旋,该如何开口呢,还是没有思路。
说到这,必须要感谢进的呐喊,周围人或多或少都知道我和进在中午计划什么,但愿他们不知道全貌。
“所以呢,绘鹰和吉原君在计划什么吗,我可听说有一些不雅致的声音呢。”
幸子安静地笑着,大概是错觉吧,我总觉得她笑得有些邪恶,就像恶作剧即将得手一般。
“这个啊……总而言之,要和我去公园走一走吗?”
被幸子率先提出这件事,也省去详细解释的力气。
冷而甜的空气混着雪花冲入鼻腔,吐出白色的雾气,我大约是在紧张吧,连脚下踩着积雪的吱吱声都听的真切。
一路上几乎没有对话,我偶尔扭头看向幸子,她嘴角常常勾起,又控制住,然后吹气看着白雾玩。
绝对是坏笑,凭借对幸子的了解,我下定论断,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难不成是我的窘迫被看出来了,那就很逊了。
“要说些什么呢,我亲爱的绘鹰君?”幸子在梅树下转了一圈,双手背到身后,身子前倾,看着我。
可恶,这种无形的压迫感和紧张是怎么回事,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要说——幸子,我喜欢你。”
“嗯嗯,我也喜欢你……没了?”幸子看着我,等待着我接下来的话。
原来告白还有下面吗,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也许看出我的疑惑,幸子缓缓补充:
“这种时候,要说无论富贵与贫穷……”
“等等,这才不是确认关系,是婚礼吧!”
“诶,好失望,那么绘鹰要做的事情只能等到结婚以后了哦。”
是和进那家伙的讨论啊,所以当时幸子就在附近吗,那我们的讨论都被……真是可怕的事实。
看着神态变化的我,幸子终于不再强忍,开始放肆大笑起来,吐出一串白雾。
在这样白色的世界里,听着幸子的笑声,我想也的确是十分值得纪念的了。
三
原想写的更多,以细致品味当时的意趣,可惜,吉原进那家伙今天找到了我。
他看了稿件,显得有些惊愕,但也没说什么,随即想要带走。我急忙拦下他,表示并没有完成。
“真想往下写?”罕见的,进没有任何搞怪,没头没尾地问了我。
我知道进在说什么,还是接过稿子,说:“当然喽,故事还没有结局呢,我买了梅子,吃点吗?”
“算啦算啦,我不想把前几年刚补好的牙硌掉。”
进转身,摆了摆手,直接离开了我的诊所。
和世界上大多数情侣一样,我的幸子在那个盼望已久的寒假,并没做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甚至在学校的记忆还能更鲜明。
若将看电影,买CD之类的一股脑写上,怕是要被嫌弃啰嗦的,故而一笔带过。
时间来到春假,我与幸子开启了第一次的远途旅行。
那是二零一六年的三月末,大阪的春假正在那时开始。
春日的阳光总是诱人的,两周的假期又是绝好的机会,在将近一周的准备下,我们踏上前往熊本的旅途。
“怎么突然想去熊本?”列车上,我向手扶窗框远望的幸子问。
“不想看看熊本城和那里的樱花吗?”
不假思索的,幸子随口回答。
这的确是极有说服力的答案,古城的樱花就是会更加壮美。
即使数码科技飞速发展,可幸子总是不大感兴趣,她独爱那种小巧易携的拍立得相机,虽然不是很理解,但还是为她带着了。
后来,事实证明,幸子是明智的,以我的技术,再高的像素都是浪费,拍立得好歹真的能快些拿到相片。
抵达熊本的第一件事,自然是等待幸子找地方换好和服,没错,大部分的行李都由我来拿着。
“喂——绘鹰——”幸子站在远处,向我挥手。
“看——好看吗?”
明明可以走过来,可幸子坚持用喊的,真心感谢当时的时间尚早,四下也无多少人,否则终究是不太礼貌的。
我不会搅了幸子的意趣,便一样在远处喊。
“非常可爱!”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呆呆的,没几句就累了,于是相向而行,四月的风中有泥土的腥气,或许也有别的,是其他日子没有的气味,幸子说,那是生长的气息。
幸子先拍了些照片,净是些建筑,于是我决心为幸子拍几张,与我而言,她远比那些有魅力。
“……”看着手中的照片,幸子陷入一阵沉默。
“想笑就笑吧。”
“哈哈哈哈……抱歉,绘鹰……哈哈哈哈……但你拍的……”
幸子放肆地笑着,一面批判着我的技术,经过幸子单方面“严肃”的决定,换我被拍了。
不得不说,幸子的审美十分在行,连我都能看出这些照片之间明显的差别。
原是打算拜托别人拍合照的,却发现相纸已经用光,只得不了了之。
能大方的向他人求助,失败后又能潇洒离去,幸子的外向再一次令我拜服。
在熊本的几日,我们几乎可称马不停蹄,天守阁,本丸御殿……熊本城内说得上景点之处,都已经走遍。
“我们就要回去了吗,绘鹰?”幸子趴在旅馆的床上,看起来不怎么开心。
“当然啊,毕竟还要回去上学呢。”几乎是用哄骗的语气,我试图让幸子开心些。
“诶——可是还想去阿苏神社啊。”
幸子翘起小腿,来回摆动,拍打在床上。
大概是我也想玩,亦或是不愿看见幸子这般失落,总之,大概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任何事,就如同所有的雨天生就要落在地面的。
我徘徊两步,坐在幸子身旁。
“那,我去和先生请个假好了,我们再玩一周也好,但去了神社就要回家啊。”
“当然了!呜——我的绘鹰——”或许怪叫也是幸子的才能,她的语言仅用书面是很难形容的。
带着极度的惊喜,幸子翻身,从床上弹起,展开双臂拥向我,也许是还记得身处旅馆,又想到什么,脸色微红,就立刻松开了。
这样也好,不会让我失去理智。
请假的过程是有些阻力的,先生起初犹豫,但想到我们课业还算优秀,终是没能拒绝,即使拒绝,我想我也会带着幸子逃课的。
四
是了,朱红的楼门,古典的神社。
四月十四日,我们如期望的那样,抵达了阿苏神社。
相较前几日而言,这里实在宁静,除了人们的声音很大,几乎没有鸟雀的叫声。
我们没想太多,慢慢向上走着……
走得太累的吗?开始发颤了。
不对,这不是我的腿在抖!
“幸子!”我抓紧她的手,向下奔跑,快些,再快些……
“地震?”没有反抗,幸子和我跑了一段距离,很快猜出我的用意。
“嗯。”
奔跑,奔跑……
刺耳的声音在神社内传出,也许是横梁断裂,砸在低处。
眼前是狂乱的线条,树干在狂舞,碎石不间断从头顶砸下。我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很大伤害。
但幸运,从来是被衬托的。
我听见幸子的惨叫,耳膜的轰鸣,甚至来不及检查她伤及何处。我背起幸子,不擅奔跑的她,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会带她离开。
……
是怎么离开的呢,说实话,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有肺部的灼烧感未曾退却。
“医生!请问幸子怎么样了?医生!”
“嗯……你是她的家属?”
“算!您快说吧。”
“跑的很快,保住了性命,只是她的右臂……”
没等医生说完,我冲进了病房,讲真,这样的行为是违反规定的,也得感谢医生善解人意,没强行留住我。
幸子躺在白色的床上,身上有些细密的伤痕,她的右小臂……空空的,缠绕着好些绷带,白色的布匹内隐隐渗出红色。
“啊——绘鹰……”幸子张了张嘴,叫了我的名字,却没有说任何话,我看见清澈的泪滑下,在她可爱却悲伤的脸上。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休学在家,全力照看幸子,不知为何,她恢复的有些慢,但好在还是在恢复。
我不敢离开她,幸子常常会发抖,她说好像小臂还在,被石头压的生疼。
医生说她也许有些先天性心衰,以致心肺功能并不健全。
七月中旬,幸子第一次出院,没怎么见过太阳了,她想抬手挡光,动了两下又举起左手。
“那个……绘鹰,我现在是不是很不好看啊。”
“不会的。”我从没如此断言过,幸子在我眼里依旧有着十足魅力,可惜因为我的请假,才使她断臂。
接下来的日子,幸子偶尔会不自觉的发抖,但据她所言并非因为幻痛。
“就像有一双大手紧紧攥着我似的,呐,绘鹰,能理解吗?那是顶可怕的场景,有种会被你抛下的恐惧哩。”
她的话尽可能欢快,但掩饰不住颤抖,她常贴紧我,才勉强缓解抖动。
那时,我托吉原进帮忙买些梅子,那家伙在门外,不肯进来。
“进来啊,进,还有多谢你的梅子——但今天不是周末吧,你……”
“骑士的风度就是如此绚丽,走了,还要翻回去呢。”
我没再多说什么,目送他离开。
后来幸子吃了两个,显得很开心,但也没能吃完,在那以后,她常常是胃口不好。
“这梅子还是要你吃的,我不大能欣赏,该说有些浪费。”
“没关系的,多吃些总会吃到甜的,绘鹰,我真的吃不下去,但它的味道,还是很令人开心的。”
一直到九月份,幸子才能自行活动。
那时的幸子更加渴求我了,无论从什么角度,她几乎与我形影不离,当然,我很乐意如此,如果她能健康就更好了。
我们做了很多超越普通情侣的事,但我并不知道正确与否,但现在想来,是不后悔的。
幸子也开始慢慢进入正常状态,开始发自内心的笑了,虽然比之前更粘着我就是了。
进偶尔会来找我,这家伙总是出乎意料的敏锐,连关系的变化都会发觉,并常常以此取乐。
“喂,绘鹰,你知道结婚什么的会有倦怠期吗?各种意义上的。”
“进君,不要这样说啦……我们……”幸子的脸皮是很薄的,会在这时候脸色羞红地将他打断。
“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发觉的,难不成你按监控了?”
“啊……某些人都快贴上了,啊,现在也是。多出去玩玩吧,在家里呆着迟早会无聊的。”
看着幸子脸色愈发红润,我决定一脚把进踹出去。
“啧,这俩人……算了,我自个玩去。”
十月份我们依旧会捡些红叶,十二月依然会去玩雪,CD也是会常买的。
幸子的家人偶尔会从东京打工回来,常常感谢我的照顾,其实这真的没什么。
幸子仍爱笑活泼,进的“危言耸听”也的确让我们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只是不会去旅游了。
那时,我本以为日子会渐渐冲淡一切,直到生活回归的一切正常,却没想到,这仅仅只是开始。
来年三月,幸子偶尔会腹痛,头晕,发烧之类,期初并不严重,后来送往医院,诊断出心肌炎。
幸子家里人将她转送到东京的一个医院,我们也只能书信来往,她的字不是很好,看起来左手写字确是很大的挑战。
我与她提过发短信之类的事,可她坚持手写,我也不再多说什么。
……
五
自三月份幸子去东京开始,我常会想到她发抖的神色,便也会不自觉抖动,这或可称得上心灵相通。
说起信件么,我大抵每周能收到一封,多时能收到两封,偶尔她会提起病房外的景色,说起做的怪诞的梦,其余的便是对我的生活的想象。
幸子并不主动提起她自己的处境,除非我的回信有明确想要了解的东西,从她模糊其词中,我大抵了解她过得并不如意。
“就像处于四叠半的房间里一样咯,没什么可说的,身体和精神的渴望都被压制得死死的。”
幸子曾在五月的来信中如是提到,我多次提出要看望她,却屡招拒绝,理由千奇百怪,但好在她的回信看起来还挺有精神。
直到六月下旬,那一周我并没有收到幸子的来信,等待两天后仍没有消息,这不能不让人焦急。
在那一天里,我没有对任何人说,独自前往东京,当然,也没有请假。
凌晨时分,街灯还很昏暗,我的影子被拉的很长。
这一次,进不知晓我的行动,即使知道他大概只会劝我买些梅子去,但我觉得到地方再买也不迟。
出行路上,听着行李碌碌的声音,心里却充斥各种琐碎念头,仿佛有种力量,在阻挠我思考幸子的各种事。
再次睁眼已是上午八点,夜间巴士就快到东京的终点了,一晚的睡眠并不好,只需稍动一下,脊柱便会发出喀喀的响声。
下车后,拿着行李,问了许多人,才算乘上三田线地铁,向顺天堂医院慢慢移动。
顺天堂医院,重症监护室。
隔着玻璃,我望到了幸子,她的脸上并无血色,袖口像夏季无风的窗帘垂下。
各种当时我并不能看懂的机械闪烁光芒,揭露一个个应当很重要的数字。
“医生,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医生的眼神闪动一下,似乎有些挣扎,沉默片刻,他终于开口:“原是不可,但是现在……你去看看也好。”
我明白我可以去看看幸子了,直接推门进入其中。
其中肃穆的可怕,幸子在一群人之中躺着。
她瞧见我,眼睛动了两下,有一种奇特的光芒,至今也再没见过第二次。
我知道她是惊讶,然后是欣喜,接着我目睹她的眼睛渐渐被泪水填充,她张嘴,似乎在寻找说话的感觉。
“啊……绘鹰……你来了——我现在真想吃梅子哩,能帮我买些来吗?”她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子坚定,不疑有他,我这便奔跑下楼。
“哎……”似乎有医生在叹气,但现在并不能管这个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天之前,幸子是带着呼吸机的,已然带了有八九天,直到那一天才摘下。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来的及时,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来的太晚。
等我回来时,幸子已没了生息,她是带着微笑入眠的。
幸子的家人告诉我,她没有叹气,而且微笑的很开心,自住院以来,她很久都没笑过了——除了偶尔写信的时间。
“真的很感激你,绘鹰君,”染井夫妇向我鞠躬,“没有你,那孩子不会笑着离开的,真的万分感谢。”
啊啊,幸子走了啊,真是奇怪,我没有留下一滴眼泪,仅仅是稀里糊涂的带着一坛骨灰和一袋子没动过的梅子离开。
并没回到久住的房屋之间,我捧着幸子,来到丰能地区的祖宅。
“很漂亮的乡村啊,幸子,你会喜欢这的吧,嗯嗯,我知道,比那些没有设计感的城市强多了。”
我嘟囔着,将坛子和梅子一同埋下,在宅子的后头。
后留了一级,我最终通过了一个大学的医学部内部考试,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就在丰能地区任职。
顺带一提,吉原进那家伙成为一个不温不火的搞笑漫画主编,偶尔不务正业投些小说,或许是工作清闲,他常会来看我,要我帮他写一些。
我家附近都是些四方的田地,冬日会被新下的雪覆得很白,与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相比,填满这里的建筑要有设计感的多。
天草家的医生和他每年要种的梅树——历来是被同村的老人称道的,或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展露的外向。
“哟,绘鹰,还没写完?马上要交稿咯——”
进又来催稿了,他是知道我快写完了吗?
“马上,你这混蛋,去宅子后面自己摘些梅子吃好了,吃完我就写完了。”
“哇,这东西真的很酸涩啊!”
“那是你不够信任它。”我拿起手边的梅子,随口咬下,是甜的。
进被这一手搞得猝不及防,他站定,挠挠头,略有疑惑:“这东西能感知信任……真邪门啊。”
梅子是一种生不逢时的水果——在极寒之时开花,酷热之时结出果子,品尝之后的回忆往往只剩下酸涩。
现在,我确凿它有可爱之处了,或许梅子常常酸涩,但我们必须信任下一颗,多吃些,总会吃到甜梅子的,再者,酸涩的回味,亦是梅子所存在的意趣,我不后悔品味每一颗梅子了。
“喂,绘鹰!我吃完了,快交稿!”进的呐喊又传来了,好在我是一个守信之人,那么,便完结好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