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早拾掇了铺子,又贴了门联,敞开了店门,待着客人到来。今晚便是除夕了,每年这时几位老先生便会一聚,谈些细琐事。
我记得是有四位先生的。经商的先生是上午来的,带了些酒食。习武的先生是中午来的。而说书的先生是晚上来的。却迟迟未见拉车的先生,许是天寒地冻,身体抱恙了。可先生却不意外,似是早就料到一般,我不愿多想,也就当作无事发生。
待到人齐全了,菜也上了桌,话匣子就打开了。起头的是经商先生,因为他经商多年,心思缜密:“老几个,年年想,年年聚,这几聚几散便是四十载,我这身衣钵可要趁早传与后辈,到时天天看着哥几个才不挂念嘞。我看王老哥——先生是姓王的——眼光就是独到,也不知当年怎么寻到这娃子,可聪明着哩。”
习武先生性子直,跟经商先生两人多有磕碰。习武先生大口饮下酒水,斜眼瞪着经商先生:“卖货的,就你那些个生意哪里称得上繁忙,不尽是手下在打理?我看你是生活好了,忘了本了!”经商先生不恼不怒,笑道:“杂耍的,看在今个过节,我也就不跟你一般见识。可你吃了我的酒,就得给王老哥一个面子,便不能与我争斗了。”习武先生别过头去,大口吃着酒菜。
说书先生虽能言善辩,可心中最是畏怯,常常忧虑己身。说书先生叹道:“你俩倒是心大。这一年一聚、一聚一少,先是走镖的,又是拉车的,不知何时就轮到了你我。我怕最先是我,又怕最后是我,这该如何是好哇。”经商先生和习武先生沉默了,或手指敲桌,或脚掌拍地。
先生是几人之中的长兄,为人中正平和,无杂乱心思。先生温和地笑着:“咱们兄弟六人相识多久了?”说书先生和习武先生细细想着,只有经商先生笑着应答:“咱们结拜那日我才十二岁,自那日起已过了六十三年了。”
先生又问:“老四,还记得那日咱们说了什么吗?”说书先生稍作忆想,应道:“姓氏不同,心意相通,虽不得同日生死,但求苦难同当。”先生点头:“那时你我年纪幼小,尚能同当苦难、无惧生死。如今年纪大了,怎么怕了这些?”
酒过三巡,众人都有些醉了,纷纷起身告别。待三位先生离开了,先生却将我留下。先生向我问道:“娃子,你觉得山是什么?”我想了许久,似乎得到了答案,却像隔了一层纱,只能看到答案的影子。先生见我久久不曾回答,便换了个问法。
“什么是登山?”
“实现自我?”
“为什么要登山?”
“为了成为先生,为了赢得尊重。”
“那你有想过失败的人去了哪里吗?”
“他们离开了吗?”
“他们不曾离开,他们也无法离开。你能看到他们,你却无法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我愣了神,傻傻地望着屋外的山,似是明白了什么。想起了外环的文爷爷,想起了那座坟墓。
“娃子,你真的想要登山吗?”
我重重点头,看着先生的双眼,那双闪着光的瞳仁深处似是装满了哀伤。
“那你明日便离去吧,去往宇文先生的书院。”
先生转过身,向着黑洞洞的屋内走去。我双手伏地,向着先生跪下。
“拜谢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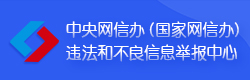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主角终于踏上征程了!还有那段对话写得很棒哦,第一次看你写对话驱动嘞~
没什么学问,更没什么眼界,只是想写些字。大佬看到了不喜欢还请手下留情,喜欢了欢迎提出观点,不要留下个让人看不懂的问号。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