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蔡决定去死,这个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村里。村里的寡妇们各个都长大了嘴巴,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这并非是她们对老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反倒是去死这种事必然是值得被惋惜的。穿着豆鞋紧裤的小年轻们路过,嗤之以鼻,毕竟他们每人都死过好几次。“在道上混是这样的”,他们说,事实也的确如此。
可能你会感到奇怪,死过很多次是什么道理,实际上也不难理解,这所谓的“死”对于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当那群二溜子被当家的薅到田地里收一上午麦子,搁谁都要死上几回。如此:累死,郁闷死,羞死,丢人死的,数不胜数,但一定都是相当的无趣。
王姨则不同,她不是寡妇,但比寡妇好不到哪去,毕竟没人像她养着自家三个娃吃饭。说起来,那三个娃还没到成为精神小伙的年纪,想来这辈子也成不了,若是他们仨感学坏,王姨是要揍死他们的,所以啊,在王姨动手之前,三个可怜娃就且先赖活着罢。不过对于王姨的丈夫李三那就不一样了,王姨最担心的,就是李三啥时候回喝死在酒桌上。
李三是个村干部,他的工作就是和上面来的领导一起喝酒,至少王姨是这么认为的 了,要是李三啥时候喝死了,也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可对于李三来说,他早已经死过几百回了:就拿他仨月前那次来说,他那三个儿子把他从大马路上抬回家的时候,王姨都忍不住寻思在哪里买寿衣会比较实惠一点儿。这当然是值得考虑的,毕竟,人这一辈子,再怎么死也不能穷死吧。
但你若说真有穷死的不,那想必是有的罢,毕竟村子不算富裕,乡里乡亲们有了啥好处,首先就得自个儿藏好喽,防着那些周遭邻里住着的那些豺狼虎豹。我就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吧:村东的王五结婚的时候,村里人可是都来了,可惜的是彩礼没收到多少,饿死鬼却来了一堆。饿死鬼们是不怕死的,如同蝗虫过境一般席卷,所到之处连颗菜叶子都不剩,他们不怕死,但王五夫妻俩可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就是不知道他们之后是否如愿,但现在看来,大体是未能如愿的,也是好事。
寡妇们说这事的时候,最里面带着玩味,但又不得不生出悲悯来,大概死亡的确是让他们觉得可惜的,但至于为什么可惜,她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况且也从来没人会这么问她们。若是真有好事者问她们这些,遭她们每人一白眼,差不多是要尴尬死的罢。如此以来,村里的“惨剧”便又多了一回。“这可算不上什么好事”,王姨说道。
但若是说村中人怕死吧……那倒也不对。就比如说上次,一伙子寻衅滋事的臭流氓来村里闹事,那帮小伙子们冲的比谁都快,完全是一股子往死里拼命的劲儿,最终把那帮怕死的流氓屁滚尿流的赶了出去。小伙子们乐坏了,他们成英雄啦!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大事件,尤其是撩小姑娘的时候,特好使呢。不过往长远来看,终究是明天上午要死在麦田里的一帮子人,也不值得有什么稀奇可言。
说来也奇怪,仿佛村里人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死不死的薛定谔叠加状态。死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李三对此最有话语权。可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的主题究竟在哪里呢?许多文人谈到死亡时候,所表现出的情感往往是阔达的,作为一种所有生命到达时间尽头的一种通用泛式,足矣让心怀浪漫的人浮想联翩。它是一件小事,小到所有人都得经历一回;它也是一件大事,大到所有人都必须体验一番。
我曾经问过几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他们当然是没什么文化的,但是说起死的事情却是毫不逊色了,有的老头子,甚至连寿衣和棺材都给自己买好,生怕自己死的时候别人敷衍自己,如同过生日时在商场锁住一个布娃娃不放的小姑娘似的。对于死亡,他们毫不避讳,如同死亡是自己最亲最近的朋友,相比寡妇谈论死亡时挤出来的悲悯,老人儿的情感却要更自然一些,这大概是没什么文化的老人们独有的浪漫情怀罢……至于我,我自然是怕死的,我嘛……我就尽量活,活出精彩,死亡这种事就等老了之后再说吧!
至于老蔡,他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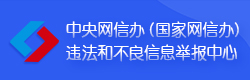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有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