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时那个叫露可的女生,像一株生长在校园角落里的含羞草,安静,敏感,稍一触碰,仿佛就会收紧所有叶片。她总是坐在教室靠窗的倒数第二排,那是优等生与喧嚣地带的缓冲区。她的存在感很稀薄,稀薄到如果哪天她没来,可能要到下午第二节课后,才会有人不经意地问起。
她的校服总是洗得比别人更白一些,领口和袖边带着一点点磨损的毛边。她走路习惯性地含着胸,长长的刘海常常垂下来,遮住大半张脸,只留下一个清秀而疏离的下巴轮廓。她很少主动说话,被提问时,声音也像蚊子哼哼,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大多数时候,她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看着操场上的奔跑,看着天空云卷云舒,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的忧郁。
男生们私底下偶尔会议论她,说她“挺不错”,但也不得不承认,她身上有一种别的女生没有的、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气质。女生的小团体里,她也始终是那个边缘人。不是没有人试图向她伸出过友谊之手,但她总是像受惊的小鹿,用最礼貌也最坚决的方式回避开。久而久之,大家便也习惯了她的独来独往。她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书本、窗外的风景,和一个谁也进不去的、秘密的内核。
直到高三那个兵荒马乱的春天。
一次模拟考后,成绩下滑得厉害,班主任决定来一次“乾坤大挪移”,彻底打乱座位。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露可被调到了你的斜前方。
起初的几天,依旧是沉默。你们唯一的交集,可能只是传递作业本时指尖的轻微触碰,她会飞快地缩回手,低声道一句“谢谢”。
打破僵局的,是一本掉落的笔记本。
那是一个午休时分,教室里大部分人都在伏案小憩。她起身时不小心碰掉了桌角的笔记本,厚厚的,牛皮纸封面,没有写名字。本子摊开在地上,你下意识地弯腰去捡,目光却在触及内页的瞬间,凝固了。
那不是课堂笔记。
纸上,是密密麻麻、纤细而有力的钢笔字,构成了一篇篇短小的故事或随感。更令人震惊的是旁边的插画——用同样细致的线条勾勒出的奇幻世界:长着翅膀的鱼在云层中游弋,藤蔓缠绕着废弃的钟楼开出星星状的花朵,一个背影孤独的女孩坐在巨大的蒲公英上,即将飘向远方……画风诡谲而美丽,充满了磅礴的想象力和一种近乎哀伤的诗意。
你愣住了,几乎无法将这些画作与眼前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联系起来。
她惊慌地转身,看到你手中的本子,脸瞬间变得惨白,一把夺了过去,紧紧抱在胸前,像守护着世间最珍贵的秘密,眼神里充满了被窥视的恐惧和一丝……决绝的防御。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慌忙解释。
她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咬着下唇,坐回座位,将背影留给了你。
你以为,你们之间那扇刚刚裂开一条缝的门,又被彻底关死了。
然而第二天,当你从书桌里拿课本时,一张折叠成方块的纸条飘落下来。打开,上面是她清秀的字迹:
“请不要告诉别人。谢谢。”
后面,还跟着一个极其简单,却让你心头一动的铅笔涂鸦——一朵小小的、正在合拢的含羞草。
就是从那张纸条开始,你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而隐秘的联系。你们从不谈论日常琐事,也不聊高考的压力。交流只在纸条和那本偶尔交换的“秘密笔记本”上进行。你会在她的画作旁边,写下一段你读到的诗;她有时也会在你某篇潦草的随笔后,画上一幅小小的插画作为呼应。
你渐渐知道,她来自一个沉默的家庭,父母常年在外奔波,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将她包裹。而写作和画画,是她唯一的浮木。在那个本子里,她是她自己国度的女王,自由,强大,无所不能。
“只有在笔尖划过纸面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是真实的。”她在某张纸条上这样写。
高三的时光像按了快进键,在无数的试卷和倒计时中飞逝。最后一次换座位前夕,她突然在放学后叫住了你。教室里空无一人,夕阳的余晖将一切都染成暖金色。
她递给你一个用画纸精心包裹的长方形物件。
“送给你。”她抬起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直视着你的眼睛。她的眼睛很亮,像蒙尘的珍珠终于被擦亮,里面没有了往日的怯懦,只有一片清澈的、温柔的坚定。
你拆开,是那本牛皮纸笔记本。扉页上,她写着一行字
“给唯一读过我故事的人。谢谢你,让我的沉默不再是独白。”
一个女孩,独自坐在教学楼的天台上,望着远处沉入都市森林的夕阳。她背影很小,天空很大,但有一种无声的、并肩作战的温暖。
那一刻,你忽然明白,高中三年,你可能错过了许多热闹的友情和懵懂的爱情,但你却无比幸运地,窥见了一个灵魂最为璀璨和真实的模样。
后来,一个学期结束,大家各奔东西。露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城市,读了一个与美术相关的专业。你们没有再见过面,也极少在社交软件上交谈。她的头像始终是灰色的,朋友圈也一片空白。
但你知道,她一定不再含胸低头,不再用刘海遮住眼睛。她或许正背着画板,行走在陌生的城市,用她的笔,继续构建着那个瑰丽而自由的王国。
那个叫露可的女生,她不是任何青春故事里典型的女主角。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艳时光的容貌,她只是安静地来,又安静地走。但她像一颗温柔的彗星,划过你青春记忆的夜空,那短暂却璀璨的光芒,足以在往后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提醒着你:
每一个看似平淡的躯壳下,都可能藏着一个波澜壮阔、深不可测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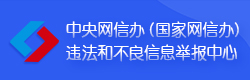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好看
喜欢
写的真好![[stick-7]](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new/喵浅-委屈.png)
楼层为空,别让楼主寂寞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