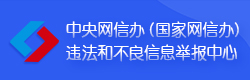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青蛇】“眼生的亲切……你我只是素不相识的的陌生人,何以一见如故?”
青玉簪面不改色,亦是将金蛇的话当浮于表面的客套话,已是见的多了,自然难以动容。翠衣纷纷,她手袭着一面灯笼走在前面引路,笼内的微光烛火跟着步伐上下摇晃,像是欢快的鲤鱼在晚野,在藻间嬉戏打闹,游进了行宫里“真”字走廊,能俯瞰全景,山腰有两道璇瀑布,水流湍勇,但不烈,是有假石在其中阻隔,恰到好处。
过了“真”字走廊,两人到了一处清水别院,别院正中间有座小庙似的道堂,偶然间能嗅闻到一丝遗留的香火气,四角种着无名道出的小白花,像是茉莉,又像是百合,在夜晚里潺潺绽放,还在花瓣上顶立着微弱的莹光,一片清凉宁静,仿佛像是某位大人物归隐的去处,可仔细一瞧,能见道堂的牌匾上写着“论经堂”。
青蛇推开论经堂的板门,里间家具没甚么缺陷的,她率先走进去,从橱柜里拿出套被褥一指,说道
【青蛇】“今后你可暂居在这儿,金姑娘你穿着华贵,别嫌弃寒颤,这论经堂可是数年前玉女派的千师太和天游派赵掌门坐而论道的地方,以此得名,姑且称的上名居罢。”
青蛇替金蛇铺好床铺,又忽然朝上面一坐,两只嫩红干净的小脚延伸在外,伴着身体在床上翻滚起来,搅的头发凌乱,和在家淘气的小女孩一样,那姑娘从被褥中抬起头,发现金蛇正饶有兴致的盯着自己,才意识到这里并非自个的居所,顿时小脸泛红,跳了下来。
【青蛇】“那………我住的地方不远,你碰着什么问题,来旁边找我便是了。”
【金蛇】“咦?”金蛇故意低声问道【金蛇】“这论经堂庞大,只有我一人?还以为青姑娘你也住这,才会这番不客气呢。”
【青蛇】“你!”
青蛇被揭了丢脸的事情,羞愧的更加生恼,她本就心思单纯,又性如烈火,便没好气的回应道:
【青蛇】“哼,我初来夫人身边时,就是安排论经堂给我居住,可是这里甚是无聊!古人喜好高山流水,渔歌唱晚,我却觉得好生奇怪,住在这古板没趣,不好玩,不好玩,他们常说我是个野丫头,嘿,我就在旁边的东崖上自己动手修了个茅庐,不比这论经堂好?”
她讲到后面,竟然自己乐了起来,还真是个容易自我满足的“野丫头”。她走到桌边,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东西,拿起金如意放在那的酒葫芦就是给自己倒了一杯,道:
【青蛇】“金姑娘,如果住在这有闷了,不妨到我的茅庐聊聊天,我也怕没人说话呢,你来了其实也好。”
金蛇点头答应,同时拿起自己的酒葫芦,开怀豪饮,酒液自唇角溢出些许,流到胸怀处的衣襟,湿了布料,却更是可人
【金蛇】“和我聊天嘛,呵呵,我自然是随意,可玉女峰上谈修养亦或是你口中的‘有趣’,厉害的人应是不少,我非最佳人罢。”
【青蛇】“他们?呵。”青玉簪摇了摇头,毫不掩饰轻蔑之情,【青蛇】“他们怕我,遇着一言不合的,有被我打残的,有被我打哭的,远远的听见我的声音,便已经六神无主,懦夫而已。嗯,夫人说,金姑娘你武功不错,将来我们要是打起来,就算事以翻篇,你也肯定不会和他们一般,对吧?”
金蛇心想,比起她来,这小家伙还真是从心所欲,纵情快活,不像世间诸多人,拘泥礼数等表面功夫,实际上心思阴暗,蛇蝎心肠,背地里打着不知道什么可怖的算盘…………似自己金如意一样。
想到这,她看向青蛇的眼神多了几分欣赏,走到青蛇面前,用手帮她梳理好头发,认真说道:
【金蛇】“你呀,何必出口都是打杀,长此以往,谁会和你做朋友呢?”
青蛇顿一顿,笑道
【青蛇】“将来如果能遇到一知己,自然不用刀剑讲话,至于朋友,但愿少些,精些,就极好了。”
【金蛇】“如此豁达的言语,从你口中说出,教我自愧不如啊,只是没想到青姑娘为人清醒,居然也会奢求那白蛇血肉。”
那青蛇桃嘴一撇,立刻反驳道:
【青蛇】“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我认为真理,就连女娲都不能逃避,要是这个世界上真有能轻易长生的法子,依我看,不过是邪魔外道。”
【金蛇】“这点上你我想的一样,但你做了夫人的侍女,难道不是为了那东西?”
【青蛇】“才没有呢!我……我……我………我自有原因,不用你管!”
她连哼数声,快步的拍门而去,然而才出几步,她又忽的停了下来,金蛇以为她还有话要说,正要倾听,谁知那青蛇却是拉起自己眼皮,愤愤的吐出舌头,对着金蛇做了个莫名的鬼脸,随后迅速的跑开。
金蛇无奈摇头,权当是青蛇在闹小孩子脾气,并未放在心上,转身打量起这论经堂来。堂内陈设简素,正墙挂着一幅泛黄的《山水论道图》,笔触古拙,想来是玉女派遗留之物。两侧木架上堆着些残破典籍,多是讲些调息养生的法门,她随手翻了两页,便觉无味。
目光流转间,忽见墙角案上斜倚着一把古琴,琴身是陈年老桐木所制,琴面泛着温润的包浆,弦虽未上紧,却无半点朽坏之态。金蛇心中一动,缓步走过去,指尖轻抚过琴面的冰纹断,触感细腻,竟是把难得的好琴。
她寻了块蒲团坐下,将琴端正摆好,指尖拨弄琴弦试了试音。初时音微涩,待她以妖气悄然灌注,琴音顿时变得清越悠扬,如涧泉鸣石,绕梁不绝。金蛇眸色渐柔,忆起当年在苏州园林听人弹过的《梅花三弄》,便抬手按弦,转轴拨弦间,琴音缓缓流淌而出。
初时琴音清冽,似寒梅初绽,傲立雪中,透着几分孤高;渐而节奏转疾,如寒风呼啸,落雪纷飞,梅枝在风雪中摇曳却不折,自有铮铮傲骨;末了音渐舒缓,雪霁天晴,梅香浮动,余韵悠长,似有无限意趣藏于其中。
堂外夜色渐深,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金蛇身上,映得她墨色纱衣泛着微光。指尖起落间,琴音与殿外的风声、远处的瀑布声交织,竟让这清冷的论经堂添了几分暖意。她沉浸在琴音里,暂忘武夷山的诡谲局势,也暂忘心中的算计,只余下这一曲《梅花三弄》,在寂静的夜里道出千年来的心酸往事与忧愁。
曲尽,她手执烟枪挑起酒壶,把剩余的酒水一饮而尽,渐渐等到困意袭来,竹外二三夜莺忍不住邀足嗓子来了几句轻唱,悦耳动心。这般意境下,竟把金蛇苦恼多年的心火翻涌病给暂时退却,她柔缓的把衣裳解下,换绛睡袍,侧身躺在床榻间,不久终是合璧眼眸,遁入了许久未做的美梦里。
过了良久,大概是在寅间的时段,金蛇猛的从床上惊醒,她脸挂冷汗,俨然是从美梦堕落进了噩梦,四下快速扫去,除了这空荡荡的房间,便是只有自己了。她露出苦笑,重新躺下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便拿起烟枪点上一根,站在院间享受凉风吹拂。
凉风
好一阵风!
且觉风调不变,但金蛇对于黑暗向来是敏锐的,耳中除了狂风巨浪席卷的声音,还有一丝诺隐诺现的呼吸声,究其来源是从远处的墙内传来的,很快就落在水池的假山上,金蛇纵身一跃跳至房瓦,心中知道来者躲在假山后面不肯露面,便对方向喊话道:
【金蛇】“飞檐无声,运气醇厚中正,是哪路高手不敢见人?”
那无名氏察觉自己的踪迹已然被金蛇发现,就从假山后飞身疾走,好轻功,足尖在假山石棱上轻轻一点,身形便如纸鸢般掠起,衣袂翻飞间竟不带半分滞涩。他未循常理直掠天际,反倒借着廊檐斗拱的遮挡,身形忽左忽右,似惊鸿穿柳,又似夜枭踏枝,每一次起落都恰好避开月光,身影在暗影与廊柱间飞速切换。
更奇的是他运功之法,足尖点触之处,瓦片竟无半分碎裂,连风声都似被其内力巧妙引开,唯余一道极轻的“咻”声,只留下一道淡如青烟的残影。
而金蛇千年修习,虽各家武学皆有涉猎,但单论轻功,她实在未有惊世的才能,钻研苦练下也不过三流水准,哪里能追的上眼前的轻功高手?眼见追出了论经堂,那无名氏的影子是越来越远,金蛇心下一急,速把手中烟枪变为如意法宝本相,念到一句:
【金蛇】“显灵。”
自如意内吐出的一口凛冽寒气只在眨眼间便追到了无名氏跟前,冰呼长啸,待那位无名氏反应过来时,自己的退路已经被寒气彻底冰封住了。
【金蛇】“高人,莫要急嘛,不如先坐下来陪眼前的美人喝上几杯酒再走?”
那无名氏退路被封,身形骤然顿在廊檐之上,勾勒出七尺有余的硬朗轮廓。宽肩窄腰,虽着一身墨色劲装,却难掩肌理间藏着的粗犷力道,倒似常年舞刀弄枪的武夫模样。应是个男人,却是看不出面貌。
他转头时,唯有一双眼睛露在黑布之外,瞳仁在夜色里亮得惊人,锐利如鹰隼,直勾勾盯着金蛇手中的如意。见寒气凝而不散,竟未露半分慌乱,只是举起手指了指金蛇手中的如意,用厚重沙哑的声音问道
【??】“这就是那如意宝贝?”
【金蛇】“哎呀,高人对小女手上的宝贝感兴趣呀,呵呵,不是刻意来找我喝酒,那倒教人伤心呢。”
【??】“我不妨直说来意,这如意宝贝我甚是喜欢,想借来看看!”
话音刚落,无名氏忽从耳朵中掏出个绣花针大小似的什么东西,只听“嗡”的一声轻响,“绣花针”骤然暴涨,竟化作一柄三尺青锋宝剑。剑身在月光下泛着冷冽寒芒,剑脊上隐约刻着细密纹路,似是道家符箓,甫一现身便带起股凌厉剑气,直逼金蛇面门。
他身形虽显粗犷,出剑却快得惊人,招式干脆利落,无半分拖沓。剑风裹挟着廊下夜露,如骤雨般往金蛇周身要害刺来,显然是想速战速决,直取那柄如意。
金蛇不甘示弱,手中如意也变为一把一尺七寸的短剑,横在身前一档,两剑相交,无名氏只觉得拿剑的手臂酸麻,仿佛有百万斤的流水自金蛇身上发出,自己反而快要抵挡不住,大喝一身,青锋宝剑轮转不停,却全都是虚招,唯独那一剑真意朝着金蛇的眼珠刺去,然她背身后挑,万般真气聚在短剑上,乘着随意打出来的剑招随势挥去,把无名氏震的飞出数尺之外。
【??】“这是…………”
【金蛇】“恒常虚静功。”
【??】“骗人!这哪里像恒常虚静功,我又不是没读过书。”
金如意听着这人讲话奇怪,可又说不上来。
古人云,恒先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熙。又云,在阴不腐,在阳不焦。此为恒常虚静。
这恒常虚静功,是几千年以前的古早内功,虽然失传,但普普通通,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地方,压根是“不入流”的。只是百年前金蛇受心火翻涌病的困扰,为了保命无意间得到恒常虚静功心法残卷竹简,就运用自己毕生所学的各家内功、静功取长补短,自创改良了一种“恒常虚静功”,其威力更甚,好似江河,进可汇入汪洋,退可积于容器,千变万化,源流不绝。
【??】“哼,管你用什么,再来打过。”
这次他剑招陡变,不再追求极速刺击,反而剑势沉凝,青锋在月光下划出半圆弧光,竟是以剑使刀法。狂野的刀法扫过廊下花丛,花瓣应声碎裂,足见其内力也不弱。
金蛇脚下轻点瓦片,身形如柳絮般向后飘开半尺,手中短剑斜挑,不与对方硬撼,只顺着剑势轻轻一引。她周身真气流转如溪,看似散漫,实则将“恒常虚静功”的“静”字诀发挥到极致——任对方剑势如惊雷,她自守得如古井无波,短剑游走间总能精准点在对方剑脊薄弱处。
这无名氏学物,竟也同我一样杂,最开始用的是峨眉派的“银顶报国”,现在却使脚行的“走路刀”,看不懂来历,我还一时拿不下他,金如意边抵挡边寻找破绽,好在无名氏学的杂而不精。两人斗了约三四十回合,“叮”的一声脆响,无名氏只觉手腕又是一阵酸麻,刀法不由自主地偏了半寸,险些劈在廊柱上。他又惊又怒,猛地旋身变招,青锋剑影陡然密集,剑招虚虚实实,时而攻向面门,时而直取心口,时而又转向下三路,竟将一套快剑使得密不透风,连影子都似被剑影切碎。
金蛇却不慌不忙,短剑在她手中化作一道墨色玄机,时而如涧泉绕石,避过凌厉剑势;时而如寒潭凝冰,骤然挡住要害攻击。她步法看似随意,实则踩着某种玄妙韵律,每一步都恰好避开剑风,衣袂翻飞间,竟还能抽空瞥一眼对方露在蒙面布外的眼睛——那双眼眸虽锐利,却已隐现焦躁。
【??】“烦死了烦死了,只会躲来躲去,一点都不爽快!”
无名氏猛地弃剑变掌,左掌带起劲风拍向金蛇左肩,右掌则暗藏杀机,直取她手中短剑。他显然是想以近身搏杀破掉金蛇的游斗之法。
金蛇唇角微勾,她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便立马将短剑抛向空中,运起恒常虚静功的内力收缩在肾脏,待无名氏已近在咫尺之间,又将积蓄在肾脏的内力冲灌四肢,使起了自创的“金翠流光掌”,掌力柔匀鬼魅的飘过了无名氏的手臂,拍在了他的小腹处。
【??】“呜…”
无名氏闷哼一声,显然是吃不住金翠流光掌的疼,脚下无根,很快就跪倒在地上。
金如意甚是得意,右手朝空中随手一探,那柄短剑就落回到手心,稳稳停在无名氏颈侧。
【金蛇】“如何,这样便爽快否?”
话音未落,那无名氏忽然猛地抬头,黑布遮掩的唇间骤然射出一道紫红色毒液,如暗箭般直逼金蛇面门!毒液裹挟着刺鼻腥气,显然剧毒无比。
金蛇惊觉不对,身形下意识向后急掠,足尖在瓦片上借力一蹬,整个人如花蝶般翻身后退,堪堪避开毒液——那毒液落在她方才立足之处,瓦片瞬间冒起邪烟,蚀出几个黑洞,可见其毒烈。
趁这间隙,无名氏猛地翻身跃起,右手握拳,周身真气骤然暴涨,竟带着破风之势砸向身后冰封的退路。“嘭”的一声巨响,坚冰应声碎裂,飞溅的冰碴中,他足尖一点,身形如离弦之箭般窜入夜色,只留下一道沙哑的咆哮:
【??】“金蛇,这如意我迟早会取走的!”
金蛇落地时,指尖还残留着方才闪避时沾染的毒雾,微微发麻,亏有恒常虚静功护体,才不至于伤她太多。
但金如意哪会这么轻易的善罢甘休?只怕是无名氏也和她一般想法,来日指不定会趁她不设防时偷袭夺她法宝,应赶紧除之后快,杀了他!免得夜长梦多。
刚刚金翠流光掌打在他身上,令他妖气四溢,来不及收拢到五脏六腑里,正是粗心的破障。金如意沿着无名氏遗留的妖气勉强跟了一路,不知不觉已经天明略微见晓,盛红的太阳露出头颅。
追至一条木间狭巷,虽能见着晨光,但这条小巷子因过于狭窄,且两旁高处都有宽阔的木檐遮挡,所以依旧阴暗,潮湿。
【金蛇】“断了?前面是什么可以藏身的地方?”
她不禁警觉起来,手中短剑背跨而立,准备快速穿过小巷,呼听着“哎呦”,像是撞到了甚么人物,绷紧状态下的人往往会做出下意识的自卫行为,而金如意也竖起短剑,愈要朝前刺去。
短剑刚要刺出,金蛇忽觉眼前人影熟悉,忙收住势道,剑尖堪堪停在对方颈前半寸。抬眼细看,晨光从巷口斜斜照入,映出那张带着几分懵懂与愠怒的脸——是昨夜那个率真又带点野性的“野丫头”。
青玉簪被撞倒在地上,许是没回过神来,她一双素足斜收在裙角,整个人都像是小猫缩成团,娇滴滴的模样忍不住令人心生怜意。
她明了面前有人,就赶忙用手里的云画蒲扇遮挡住面容,亦不知用意何为,如此扭捏,莫非活久了还怕见人?

【金蛇】“哎呀,不好意思青姑娘,我走路急了些,撞疼了没有?”
发现站在面前的来者是金如意,青蛇长舒了口气,幸然的把遮面的扇子放下来,大声的质问道:
【青蛇】“金蛇!这么早了跑到这边干嘛,撞到人了也不懂道歉。”
【金蛇】“失礼了,失礼了,我初来乍到,这行宫内有诸多地方不了解,才出来走走。”
她伸出右手,愈有缓和关系的想法,然青蛇却犹豫不决,思考再三后,终不情不愿的让金蛇把自己扶起来。
【青蛇】“好吧,你……嗯,就当我胡口乱言,金姑娘是要到东崖去罢。”
【金蛇】“东崖?”
【青蛇】“对啊,过了这条巷子就到东崖了,要不要去我的草庐看看?”
【金蛇】“谢谢青姑娘的好意,我无非随意逛逛,不好多叨扰,先行告辞。”
【青蛇】“哦,好吧。”
金蛇拱手作别,转身便往巷外走,心思却全在那无名氏身上——方才青蛇出现在这偏僻狭巷,偏偏又是无名氏妖气断绝之处,她虽瞧着率真,可万一……念头一起,金蛇就隐约猜到了几分缘由。
正思忖间,她已走出狭巷,行了约一柱香的时间,抬头却愣了神——眼前哪是来时的路?晨光下,错落的石壁连成一片,土坡挂着的杂草陌生又刺眼,脚下青石板路蜿蜒向深处,竟不知通向何方。悲也,真该在刚刚让青蛇带自己回去的。
金蛇望着眼前陌生的石壁荒坡,眉头拧得更紧,这行宫布局竟如此复杂,不过一柱香的功夫,竟彻底迷了方向。她沿着青石板路又走了半刻,周遭愈发寂静,连方才偶尔能听见的虫鸣都消失了,只有风刮过杂草的“沙沙”声,透着几分诡异。
正焦躁时,脚下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笃笃”声,像是有人在地下敲击砖块。金蛇心中一动,俯身将耳朵贴在路面,那声音愈发清晰,还夹杂着模糊的人语,似是有人在低声叫骂,只是隔着土层,听不真切内容。
她指尖凝聚起一丝真气,轻轻点向砖块缝隙,只觉下方中空,竟似有地道。金蛇环顾四周,见无人踪迹,便运起恒常虚静功,指尖真气化作细冰,顺着砖缝轻轻一撬。
“咔嗒”一声轻响,一块青砖被撬起,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淡淡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洞下的叫骂骤然停了,随即传来一声警惕的低问:
【竹子蚕】“谁在上面?”
金蛇不想多言,只是好奇的反问道:
【金蛇】“你又是谁?”
地下的那人“嘿嘿”的冷笑两声,又瞬间变成豪迈的大笑:
【竹子蚕】“嘿嘿,哈哈哈哈哈哈,你不知道我?你给那贱人卖命,你不知道我?爷爷当年的名号武夷山哪个不知道………等等,你不是蛇妖,你是人?奇怪,我被关了快三十年了,有人?嘿,有人!”
金如意以为这底下关着的应是位狂妄的疯人,居连人与妖都分辨不清楚,正要走时,却注意到混绕在周身的是一股淡淡的清气,顿时焕然大悟,对啊,自己运动恒常虚静功时,会把自己的妖气走过幽府,肾脏,最后所使出来的内力通常和修行的道士无异,是一股清气,难怪底下的人会把她当人看。
而从那人口中的话判断,所谓的“贱人”大概是指蛇妖夫人,且厌恶到此,便计上心头,狡黠之色藏于心底,佯装道:
【金蛇】“我是人,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嘞,我这个‘人’是来找人的,不知道是不是你?”
【竹子蚕】“找人?你是何门何派的,来找甚么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找谁呢,还会告诉你?金蛇心里讥讽道,又继续说:
【金蛇】“我家师父不肯说,就教我找到就行,说是我们本派的长辈。”
底下那人自言自语的嘀咕着,那金蛇的妖耳何其聪慧,一字不落钻进耳中:
【竹子蚕】“长辈………当年的确有几个其他派狗崽子逃出去,但他们记恨我配合那贱人把攻山的人放进来的,除了寻仇,肯定不会再教人寻我的踪迹。莫非是我三仰派的师兄弟?何通否,还是元通霸?”
他声音里藏着难掩的激动,连带着呼吸都急促了几分,紧接着便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似是在摸索着靠近洞口。金蛇唇角勾起一抹浅笑,心中已然明了,这地下关着的,竟是当年武夷三十六派幸存的旧人,看这情形,怕是被蛇妖夫人囚禁在此多年。
【竹子蚕】“后生,我不问你师承了,你先快快把我放出来。”
【金蛇】“呵呵,别急呀前辈,这大白天的,教人发现了咋办。”
【竹子蚕】“狗儿子,你难道要和爷爷我讨价还价?”
【金蛇】“便是了,怎么着?”
金蛇的话一出,底下那人便恼了,一口福建方言又快又急,“凶茂”“脑吊”之类的粗话混着水汽飘上来,金蛇半句也听不懂,只抱臂站在洞口,瞧着砖块缝隙里透出的微光,倒有几分闲情。
洞下的骂声才渐渐弱下去,只剩粗重的喘息。金蛇这才俯身,对着洞口慢悠悠道:
【金蛇】“前辈骂人也这么有力气,小女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啊,可谓是老当益壮,好不佩服!”
【竹子蚕】“果然不像吃白食的,哼,爷爷我是没招了,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就带你去把那贱人的两件法宝给拿过来,怎么样?”
金蛇眼底的兴奋几乎要藏不住,指尖下意识攥紧了腰间烟枪,语气上却故意露出茫然之色,歪着头反问:
【金蛇】“法宝?我才不稀罕嘞,师父说修行之人,应当自我修炼在天地间,靠五色养气,不能拘泥于法宝外物…………”
【竹子蚕】“狗屁!你师父骗骗你还真信了,那两件法宝可是‘阴阳刚柔剑’和‘锦囊乾坤袋’,威力自然不必说,我告诉你,单纯吃素蛇血肉得来的不过是假长生,真长生的法子还得在这里面…………”
底下那人的话刚说到“真长生的法子还得在这里面”,金蛇忽然竖耳,远处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伴着小妖的谈笑声,越来越近,显然是巡山的妖兵往这边来了。
她脸色微变,忙对着洞口压低声音道:
【金蛇】“前辈,巡山的来了,我先撤!过几日我再找机会来见你,你且安心等着,莫要出声暴露行踪!”
洞下的那人也慌了,忙应道:
【竹子蚕】“好!好!你可千万别忘了!”
金蛇不再多言,双手扣住青砖边缘,借着恒常虚静功的巧劲轻轻一推,“咔嗒”一声,青砖稳稳归位,严丝合缝。她又快速薅了几把杂草铺在砖面上,用脚轻轻碾平,确认看不出任何痕迹,才转身快步往反方向走。
金蛇刚走出数十步,便与巡山的两个小妖迎面撞上。那小妖见她身着绛色纱衣,腰间悬着烟枪,一眼便认出是昨日新来的贵客,忙收住脚步躬身行礼:
【见过金姑娘!姑娘可是迷路了?需不需小的们引路回论经堂?】
金如意压下心头的波澜,指尖捻着烟枪轻笑:
【金蛇】“那就有劳几位哥哥了~”
待金蛇和几位小妖的身影消失在道路尽头,那处藏着地道的青砖下,又传来一阵细微的敲击声,只是这一次,却再无人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