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雪在今夜里就停歇了,天晴得大好,雪应是要化了。炉里的柴也要熄了,师父却是一夜未眠,就这么守着我。
待到我醒来,太阳已升得老高,屋里空落落的,却是拾掇得干净。桌上摆着碗,碗里盛着菜粥,盖得严严实实,摸起碗边还有些温热。
推开房门,院内积雪已铲得干净。师父坐在板凳上,温和地笑着:“醒了?”我点点头,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看着他。他戴上帽子,望着院外停靠的车子:“我要走了……”他站起身来,向前迈出了步子,可没走出几步,却又回头看来,张了张口,却也没说出什么。直到他回过头去,我终是开了口:“我会去的……”他压低了帽檐,似是笑了。
回到屋内,我仰面躺倒在床上。顶上的雪应是化了,落在地上,“啪嗒”响着,心似是动了。我翻来覆去,怎么也静不下心,便又起来了。
缸本来是在院里的,只是到了冬天怕给冻上,就给搬进屋里了。看着缸里的水,水中映出了我的模样,横看看、竖看看,怎么也不像是我。就这么看了半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早就不是他了。拿起刮刀,剃去胡须,修短头发,再向倒影看去,这才有了几分相像。
拾掇干净,换上干净长袄,倒也有了几分先生的模样。推开房门,走出院子,踏着白雪,走在村中,白花花一片,就连道路都被掩埋了,可道路早已记在心中了。
砖瓦堆砌的房子,若是在中环确是算不上奇特,可在这外环就很扎眼了。那是刘娃子的婚房,在村中算得上极好了,就连门都红得喜庆,一副旧对联贴在门外,院内扫得干净。
笤帚摆放一旁,壮硕汉子坐在院中,正歇息着。见我来了,他憨笑着挥手招呼。许是见我一身衣裳整洁,模样少了些憔悴,他喜笑的眼睛泛着泪光。他朝我呼喊道:“天寒路滑,放慢脚步,小心摔了身子。”我应道:“身直步稳,快步前行也很是平稳。”
见我俩进了屋子,嫂子虽忙着做饭,却也赶来上了茶水。小忱坐在窗边,手中摆弄着玩具,那是一辆小车子,是用木头雕的,这手艺活也只有梓老爷子会了。
刘娃子笑着问道:“山石,要一起喝点吗?”我摇摇头:“我已经停留太久了……是该上路了……”刘娃子摆弄着瓷碗,思绪繁杂:“告别吗?确是如此……五年了,是该接着前进了……”我举起瓷碗,与他相碰,饮尽茶水,相视大笑,笑时过境迁本心未改。
我起身告别离去,只见白雪早已化尽,显露出应有的道路,与记忆相照应。刘娃子站在门外,牵着小忱的手,喜笑着:“娃娃,他是你的叔叔……他是我的兄弟……”
年后,我乘上了车子,随着人潮去往了中环。车厢中坐着两位少年,他们说笑着,要赚上大钱,要买上房子,将家人接来,幸福地完满地过完一生。可当我醒来时却找不到他们了,许是做了个梦吧,一个有些久远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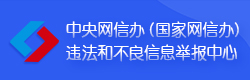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狮子之痛闪光之时![[family-3]](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2/锤子.png)
![[family-5]](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2/喝茶.png)
![[family-1]](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2/Good.png)
最新力作![[s-7]](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7.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