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夷山伐蛇战役的三个月后,天帝在寝宫里做了个梦。
梦的内容是杂乱,且毫无顺序可言,可充满了真实感。
他梦到在一个非常落后,野蛮的石屋里,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断头挂在大门。
断头张大嘴巴,并无法闭合,因为一块巨大的石头正堵在里面。
天帝走过去,想将石头从女人的嘴巴里取走,可是石头被卡的太死了,天帝只将断头的牙齿一个接着一个的敲碎来腾出空间,终于把石头拿出来了。
因为太过使劲,天帝的重心全部挤压在身后,很自然的跌倒在地,屁股传来一阵湿润。
原先堆满落叶的地面,此刻忽然变成了一条小溪。
天帝拿起手中的石头,凑近一看,石头变成了一个婴儿。
婴儿在天帝的手里哭闹着,可爱的模样令天帝忍不住想要去安抚。手即将触碰到婴儿的瞬间,一条全体发白,仿佛脊髓似的蜈蚣从婴儿的脖子里钻出来,一口咬在了天帝的手指上。
【天帝】“啊啊啊!”
他迅速的把婴儿丢在水里,害怕的后退,只见蜈蚣的半个身体还陷在婴儿的脖子里,仿佛卡在婴儿的食道上出不来。蜈蚣张开嘴巴,居然发出婴儿的哭声,仿佛在向天帝祈求奶水。
它一边哭着,一边啃着婴儿的尸体,直到剩下白骨。
【天帝】“救命………”
他在小溪里似畜彘般攀爬,还未站起来,就被莫名的拉力扯入水底。
他闭起眼睛,但水底并没有窒息感,相反,脚底似乎重新站在了夯实的大地上。
他睁开眼睛,一只蝗虫挥舞着翅膀挥舞在眼前。
一望无际的草原,他的臣民们面无表情的躺在草地上,每个人都张大嘴巴伸出舌头。
舌头在风中摇曳着,如同向阳招手的麦穗。
一片“舌头田”。
不知不觉间,起了大雾,雾是黑色的,把天帝笼罩起来,他在雾里奔跑着,想逃出这片黑雾,可雾太大了,更本走不出去。
别怕,雾会自己散开。
当雾气散开,原本躺在草地上的那些臣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表皮溃烂,在地里不断翻滚的“蛇”。
天帝之觉得身体止不住的瘙痒,他用手拼命的挠,可依旧不痛快,于是便将衣服脱下,发现自己被衣料所包裹的皮肤,居然长满了无数张脸,这些脸,来自他的臣民…………
天帝想求救,却叫不出声,他像只惊惶的兽,在蛇群中跌跌撞撞地奔跑,每一步都深陷其中,又被蛇群的蠕动硬生生往前推搡。
就在他快要被蛇群淹没时,眼角余光瞥见了不远处的身影。
那人站在草原与天连接的尽头,背对着漫天昏沉的暮色,身形孤绝得像一截枯木。穿着白衣,他的轮廓精致得不像真人,鼻梁高挺却不凌厉,下颌线柔和却带着冷意,每一处线条都美得极致,却又透着非人的疏离感——仿佛是用月光与腐骨雕成的,俊美中裹着蚀骨的怪异。
好漂亮…………
天帝暗自赞叹道,多么美丽的人儿啊。
美人笑了一下,天帝又被拉到了另一个场景。
在荒野,一个半蛇半人的女人,将那位美人按在巨大的石板上,此时,美人的四肢已经全部被砍断,赤裸的肉体正在遭受周围目光的视奸。
天帝看向旁边,几只猿猴正拍着手,欢快的尖叫着。
【女娲】“嘿嘿。”
半蛇半人的女人举起石斧,恶狠狠的劈在美人的背上,用手把美人的脊髓拔了出来。
随后,她又扯下美人的头皮,敲碎头盖骨,把里面的脑浆丢在地上,招呼猿猴们过来吃。
猿猴们尖叫的吃着地上的脑浆,渐渐的,他们褪去毛皮,改成使用双足行走,变成了“人”。
一滴血落入了天帝的眼睛里。
血海。
有人在血海里捕鱼。
钓上来一条月亮鱼儿。
异物?
是什么东西在自己脑袋里,某种情绪吗?
是………
恨!
捕鱼人重新挥洒渔网,只见无数个手从血海里伸出,想要抓住渔网,仿佛那是个救命稻草一般。巨大,强烈的怨念,把血海搅的奔涌翻腾!
血海的远处立了五根杆子,绑了五具尸体。
天帝小心的看去,好奇这些手的主人的模样。
直到他看见,海底里有自己。
【天帝】“护架!”
嘶吼声卡在喉咙里,天帝猛地睁开眼,寝殿的鎏金烛火刺得他瞳孔骤缩。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皇袍领口,后背的衣料黏腻地贴在皮肤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腥甜——像梦里血海的味道,又像茉莉的味道?总是只是出现了一瞬间,那股味道就消失不见了。
【陛下!】
殿门被猛地撞开,侍卫们手持兵刃冲了进来,铠甲碰撞的声响打破了死寂。他们神色慌张,目光扫过殿内,生怕有刺客潜伏,可映入眼帘的只有天帝瘫坐在龙床上,脸色惨白如纸,眼神涣散,还带着未褪尽的惊恐。
他大口喘着气,胸腔剧烈起伏,指尖还残留着梦里蛇群滑腻的触感,皮肤下仿佛仍有无数张脸在扭曲、蠕动,瘙痒与刺痛感迟迟不散。
【天帝】“没……没事。”
他的声音干涩沙哑,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
【天帝】“只是……做了个噩梦罢了。”
早晨的朝会,天帝坐于天椅,底下的天庭高管则依地位排序跪做。
【陛下,臣有本上奏。】
左侧列中的臣子躬身出列,手持奏本道:
【先前伐蛇战役,众门派讨要军饷无果,那巫山派掌门居然不顾天庭敕令,已在前日自立为王,称巫国,正兴兵攻来。】
三十年前各派攻打武夷山的时候,就是天庭在后面大力支持的,其本质上是把伐武夷山的工作外包给作为诸侯的各门派,但是提前说好并不出军响,而是把武夷山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各门各派。多年来各派为了武夷山的所有权可谓是争的头破血流,最后的结果是都有在武夷山驻扎自家兵马,反倒天庭能从中脱干净关系。但现在不一样,各派在武夷山经营了多年,本来天庭是打算抓到素蛇后把素蛇的血肉作为军饷犒劳各门派诸侯,可结果素蛇逃走了,各派损失巨大,自然把之前天庭做样子的文书重新翻上台面。
至于巫山派,却是有个阴谋论在最近流传开来,说是巫山派掌门早就想自立,可是以巫山派长老道敏为首的“忠天派”是最大的阻碍,于是便故意让道敏去武夷山带兵………………
【天帝】“朕不关心,你们拟旨送一两座小城给他们,自然就安抚了。对了,朕要求修的皇家妓院何时完工?”
【………………约半年吧。】
【天帝】“哦…还要这么久。”
天帝语气明显有些许不快,道:
【天帝】“加快进度吧,至少在朕一百岁生日之前,一百可是个坎,过了生日朕就算中年人了,也不能老是耍年轻人脾气,对了。”
他拍拍大腿,道:
【天帝】“到时候朕要把天后,还有后宫所有的妃子都塞到这座千古第一的皇家妓院里,朝野上下全部大臣都可以进去快活,朕把老婆分享给你们,但是得付钱啊!”
【陛下,您之前不是说只有妃子……怎么如今天后也…………】
【天帝】“你在质疑朕?不是,朕最喜欢看别人用自己东西了,这么多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们不去皇家妓院付钱,天庭哪里能让国库富裕,难怪你们拨不出去军饷。”
【但是陛下,那巫山派手下十万弟子,坐拥土地千里,当务之急是联系各派诸侯一起联合讨伐…………………】
话音未落,殿外突然传来一声朗喝,声如洪钟,震得鎏金殿柱嗡嗡作响:
【巫国使者,携国书觐见——!】
话音方落,殿门被两名侍卫合力推开,一道身影负手而立,缓步踏入大殿。此人身着玄色锦袍,腰束玉带,头戴紫金冠,面容冷峻,双目如电,顾盼之间自有一股凛然气势。身后跟着两名劲装护卫,皆是腰佩长刀,眼神锐利如鹰,步伐沉稳,落地无声,显然是内外兼修的好手。
使者径直走到殿中,不跪不拜,只是微微拱手,声音洪亮如雷:
【巫国使者,见过天帝。吾主奉天命立国,今特遣在下送来国书,劝天帝割让南部三千里土地,否则兵戈相见,玉石俱焚!】
此言一出,殿内群臣哗然。几个老臣面色大变,纷纷怒斥:
【大胆狂徒!天庭大殿岂容你放肆!】
【小小巫山派,竟敢妄称建国,还敢索要土地,简直是逆天而行!】
那使者淡然一笑,显然并无惧意,高声道:
【几位莫急也,何止巫山派,昨日,姑射山派,擎天派,亶爰派,柢山派都各自脱离天庭称王了,你们不知道吗?】
【天帝】“什么?!”
御座上的天帝猛地一拍案几,鎏金案几应声开裂,茶水四溅。方才还带着几分嬉闹的神色瞬间褪去,惨白的脸颊涨起一层病态的潮红,眼底那抹未散的惊恐被暴怒取代,皇袍下摆因身形晃动而簌簌作响。
【天帝】“竖子狂妄!一派胡言!”
天帝厉声嘶吼,声音因震怒而变得尖利,不复往日的慵懒,
【天帝】“左右侍卫,将这妖言惑众的狂徒拖出去,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殿外侍卫轰然应诺,握刀的手青筋暴起,正要上前擒拿。那使者却依旧负手而立,玄色锦袍在殿内气流中微微飘动,脸上不见半分惧色,反而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朗声道:
【我只是来告知巫国要求,本就知道天帝必会杀我,可国主何其仁德,交待虽来宣战,但亦需献上国礼,天帝不如先看看国礼,再杀我不迟?】
天帝闻言,怒极反笑,道:
【天帝】“国礼?尔等叛逆之辈,也配谈国礼?”
话虽如此,眼底却忍不住掠过一丝好奇,这使者明知必死,却仍执意献“礼”,其中必有古怪,可又怕使者行刺。他瞥了眼阶下蠢蠢欲动的侍卫,厉声道:
【天帝】“且慢!既然你要死到临头还故作玄虚,朕便容你多活片刻。但此地乃天庭正殿,岂容你随意摆弄物件?只许在阶下打开,若敢有半分异动,即刻碎尸万段!”
使者眼底闪过一抹得逞的笑意,微微颔首:
【遵天帝谕。】
说罢,他缓缓弯腰,右手探入腰间革囊,动作从容不迫,不见丝毫慌乱。身后两名护卫依旧肃立如松,双手按在刀柄上,目光警惕地扫过殿内,竟是将侍卫们的合围之势视若无睹。
殿内鸦雀无声,群臣屏息凝神,目光尽数聚焦在使者手中。只见他从革囊中取出一个紫檀木盒,使者摸着盒体,放于一位大臣跪做的位置上,眯着眼睛道:
【陛下可还记得在伐蛇战役失踪的神将无目天尊吗?】
【天帝】“嗯?里面装的是他的人头吗?”
【是天尊没错,但不是人头,而是天尊本人哦,是我们在武夷山打扫战场时发现,今天就物归原主。】
说罢,便打开盒子。
盒盖掀开时没有声响,只有一股冷腥气先渗出来,不是活物的腥,是浸在阴沟里的腐味,裹着木头受潮的霉气,慢悠悠地缠上殿内每个人的脚踝。
盒里蜷着的东西,是蛇,却又不像蛇。
它的鳞早烂没了,皮肉软得像泡发的腐木,贴在骨头上,一道一道的褶皱里积着暗褐色的脓水,正顺着盒沿往下淌,在地上积成一小滩,滩水泛着细碎的泡沫,每破一个,就散出更浓的腥气。蛇身缠成死结,尾尖搭在盒沿,尖端烂得只剩白森森的骨茬。
殿内的烛火突然暗了暗,光影落在蛇身的腐肉上,那些褶皱里的脓水泛着冷光,像无数只眯起的眼,正盯着御座上的天帝。没有声音,只有脓水淌落的“滴答”声,一下一下,敲在死寂里,像有人在数着呼吸。
这哪里是神将,是被塞进盒里、泡烂了的怨魂,连腐烂都透着不肯消散的恶意。

只见盒子里那条蛇模样的东西,在盒子中立了起来,“头”僵硬的转向天帝。
【无目天尊】“陛…下…”
那声“陛下”像锈钉戳进耳道,滞涩,拖着湿响。
天帝的瞳孔骤然收缩,梦里草原上溃烂的蛇群、血海深处的怨手、白衣美人眼底的死寂,在这一瞬间猛地撞进脑海——盒中这条烂蛇正和梦里那些蛇的溃烂创口重合,连脓水淌落的节奏,都与梦里的“滴答”声分毫不差。
【天帝】“啊啊啊啊啊,杀了他!杀了他!给朕———杀了他!”
天帝的声音刚出口就被自己的恐惧噎住。
侍卫们早被这妖异的一幕惊得汗毛倒竖,此刻得了旨意,如离弦之箭扑向使者——长刀破风的锐响里,玄色锦袍溅开一片血花,使者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被劈成两半,脏腑混着黑血泼在丹陛上,与盒中淌下的脓水融在一起,泛着噗呲响泡沫。
可那烂蛇仍立在盒中,眼窝窟窿直勾勾盯着天帝,喉咙里的“陛下”还在断续溢出,每说一个字,就有一片腐肉从下颌脱落,掉进脓水里,发出“咕嘟”的闷响。
一股只有天帝才能看到的黑色雾气,从盒中的怪物身上散发出来,迅速的跑进了天帝的鼻腔。
茉莉花的味道……………
殿角的鱼池突然暗了。
不是光影的变化,是水色沉成了墨,连池里养的金鲤都没了动静,浮在水面上,肚皮翻着惨白的光。
那墨色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是纤细的手,指节泛着冷白,没有指甲的指尖沾着黑泥,扣在池沿的青石板上,发出“咯吱”的刮擦声,像生锈的刀在磨骨头。接着是另一只手,同样的冷白,同样的黑泥,撑着池沿往上爬水顺着手臂淌下来,滴在石板上,竟不是透明的,是暗红的,像稀释的血。
然后是头颅。
乌黑的长发先从墨水里涌出来,湿淋淋地贴在脸上,遮得只剩半只眼睛。
是赤红色的瞳孔,像浸在血里的玛瑙。
美人怨恨地盯着天帝,连眼白都泛着血丝。他的脸还是那样俊美,却白得像泡发的尸蜡,唇色淡得几乎透明,嘴角却勾着一丝黏腻的笑,像刚舔过甚么。
他四肢着地,像兽一样爬。膝盖跪在青石板上,发出“咚”的闷响,露出的皮肤沾着水草的碎末,还有几道淡红的划痕,像被什么东西抓过。每爬一步,长发就晃一下,露出的脸在殿内昏暗的光里忽明忽暗,赤红色的瞳孔始终没离开过天帝,像蜘蛛一样的爬过来。
鱼池里的墨色跟着他爬动的节奏往外漫,漫过青石板,漫过丹陛上的血污,漫过那盒烂蛇淌下的脓水,融成一片黏腻的黑,像有生命的雾,裹着他的四肢,拖出一道长长的湿痕。
【天帝】“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啊啊啊啊!”
天帝看着梦里的美人此刻居然出现在现实,恐惧令他手脚并用在的皇位上乱窜,想要逃走。
可在台阶下的诸位大臣侍卫眼里,只是天帝在看到盒中怪物后精神失常,有位年迈的大臣想上去把天帝扶起,却被天帝一脚踢开。
【天帝】“你们……你们看不到吗?”
【陛下,臣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看不到…那在地上匍匐爬过来索命的美人,你们难道看不到吗?
美人已经爬到了丹陛之下,四肢撑着血污与脓水的混合物,身体诡异的对折了一下,腰肢软得像没有骨头,头却猛地转向殿柱的方向,赤红色的瞳孔透过雕纹的细缝,与天帝的视线撞个正着。
一声轻响,像腐肉被撕开的动静。美人的嘴裂到了耳后,露出一排泛着冷光的尖牙,牙缝里卡着几缕发黑的发丝。他朝着皇位的方向,以一种扭曲的姿势“折”了过来,膝盖与手肘同时着地,速度快得像一道黑影,墨色的水痕在他身后拖出长长的印子,印子里浮着细小的泡,每破一个,就散出更浓的茉莉香。
天帝吓的推开周围堵住他逃跑的大臣,滑得险些栽倒,他连滚带爬地扑向殿柱,指尖刚扣住柱身的雕纹,后背就撞上了冰凉的木。那木头上竟也渗着黏腻的湿意,像沾了美人爬过的墨色水痕。
他缩在柱后,可大臣们不理解,也不敢再上前了,因为他们的眼里根本看不到那位素蛇美人。
过了几刻时,天帝的耳边再也没听到骨头扭曲的声音,便接着殿柱的缝隙向外窥探,已是见不到那索命美人的身影。
天帝刚松了半口气,脖颈后突然泛起一阵冷。
是呼吸,正贴在他耳后。
他猛地抬头。
殿柱高处的雕纹里,那美人正像壁虎般贴在上面。长发垂下来,扫过天帝的脸颊,湿淋淋的发梢沾着水痕。他的身体完全扭曲着,四肢反折勾在柱木的缝隙里,赤红色的瞳孔正从上方垂着看他,嘴角裂到耳后的尖牙泛着冷光,牙缝里的黑发还在慢悠悠地晃。
没有预兆,美人突然松了四肢。
他像断了线的傀儡,直挺挺地往天帝身上扑——不是坠落,是“裹”,身体贴在天帝身上时,发出刺耳闷响,像熟透的果实砸在湿泥里。长发瞬间缠上天帝的脖颈,越收越紧,赤红色的瞳孔抵在他眼前,血海滴在天帝的眼睛里。
这个美人,是那天从素蛇身上逃走的黑气。
喀喇,喀喇喀喇……
那个美人空洞的眼睛像呼吸一般张开着。
【就是……你吧………那些人……都是…你…叫去…武夷……山的?】
【天帝】“啊啊啊啊啊啊!”
在各位大臣的视角里,天帝忽然倒在地上,嘴巴里不断的吐出大量的头发,在地上剧烈的抽搐着,没过会,便不再动了。
天帝死了,被“吓”死的。
恩赐六年,天帝忽然在大殿上暴毙而亡,结束了其荒淫且可笑的一生,谥号天荒帝。由太子继位,乃天厉帝,面对大军压境的巫国,天庭只能向其他门派和朝廷借兵,虽然暂时逼退敌军,可还是把柔利、无䏿等地割让给巫国。
经此一役,原先接受天庭敕令的门派也看清了天庭的衰败,权威崩塌,不久又有许多门派独立称国。
而天厉帝上位之后,不仅没有改正先帝的过错,还干了更多荒唐事。上位两年,便被宰相萧刨卷带兵砍成肉泥,扶持了天厉帝的弟弟做了新的天帝,为天灵帝。
天灵帝在位八个月,就溺水而亡,萧刨卷又立了天灵帝的小儿子做了新的天帝,为天哀帝。但是不满萧刨卷的大臣们找了几个国家拥立天厉帝的废太子在昆仑做天帝,后世称伪天平帝。于是,出现了两个天帝,两个天庭,史称“二帝并立”。
二帝并立三十多年,两个天庭互相质疑对方的合法性,直到伪天平帝那一支被姑射国吞并。天哀帝那一支则在百年后被巫国吞并。
—————————————————————————
【ps】“接下来的内容不属于正文,只是写点小番外,如果不想破坏这章的氛围那么看到直线就行。前面天荒帝的荒唐大家也见过了,现在写点他儿子天厉帝的荒唐事,算是让这个世界观更鲜活一点。
史书记载:
厉帝耽龙阳之好,尤嬖耋老。时尚书伯礼设宴于第,朝士咸集。酒酣,帝顾伯礼之父,年逾百旬,发鬓皤然,竟属意焉。不顾群僚瞠目,礼仪荡然,直前执其臂,逼而乱之。左右战栗,莫敢仰视。伯礼伏地叩首,血流于地,恳请宽宥,帝不为所动,肆其淫威。事毕,傲然还座,举觞自饮,谓众曰:“此翁虽老,风骨犹存,胜却少年千万。”满座默然,皆怀震怖,莫敢发一言。
(天厉帝沉迷男色,尤其宠爱年老的男子。当时尚书伯礼在家中设宴,朝中官员全都前来赴会。酒喝到尽兴时,厉帝瞥见伯礼的父亲已是年过百岁的老人,头发胡须都白得像霜,竟然对他动了心思。
他全然不顾众官员惊愕的目光,将礼仪抛到九霄云外,径直上前抓住老人的手臂,逼迫他行苟且之事。左右侍从吓得浑身发抖,没人敢抬头看。伯礼趴在地上不停磕头,额头磕得鲜血直流,恳请皇帝宽恕,厉帝却毫不动心,肆意发泄淫威。
事后,他傲然回到座位上,举起酒杯自顾自饮酒,对众人说:“这老人虽已年迈,风骨却仍在,比那些少年人强上千万倍。”满座的人都沉默不语,个个心怀恐惧,没一个人敢说一句话。)
史书记载:
帝自以罪愆累积,欲修功德以赎,常于天河放流群鱼,冀消宿孽。久之,谓鱼鳖之放,功德浅薄,不足弭过。乃突发奇想,欲以生人投河,谓“放生人形,福泽更隆”。
于是颁诏天下,征募新娶男女,不论良贱,悉令诣阙。旬月之间,四方辐辏,俪偶云集,凡数百人。帝亲幸天河之畔,命左右执而投之。洪流奔涌,浊浪滔天,男女号哭震野,抓揽舟舷,十指流血,终为怒涛吞噬,溺死者十之八九。
左右或有谏者,谓“生人非鳞介,投河实乃虐杀,恐干天和”。帝怒而斥之,曰:“朕为赎愆,何惜此辈!”遂竟其行,河上尸骸漂浮,水腥混杂哀魂,两岸观者莫不股栗。
(天厉帝自认累积了太多罪孽,想要通过做功德来赎罪,常常到天河里放生鱼群,希望能消除往日的恶行。时间一久,他觉得放生鱼鳖的功德太过微薄,不足以抵消自己的过错,于是突发奇想,打算用活人生祭投河,还说“放生人的性命,能得到的福泽会更加深厚”。
随后他向天下颁布诏书,招募刚结婚的青年男女,不论身份贵贱,全都要前往京城报到。短短一个月内,四面八方的新婚夫妇纷纷汇聚而来,一共来了几百人。天帝亲自驾临天河岸边,命令手下将这些夫妇抓住,一个个投进河里。天河中洪流奔涌,浑浊的浪涛直冲天际,被投河的男女痛哭哀嚎,声音震动原野,他们拼命抓住船舷,十指都抠得流出血来,最终还是被汹涌的波涛吞噬,十个里就有八九个溺死了。
身边有大臣上前劝谏,说“活人不是鱼虾之类的鳞介生物,把他们投进河里其实是残忍杀害,恐怕会触犯天道的祥和之气”。天帝大怒,斥责劝谏的人说:“朕是为了赎罪,何必怜惜这些人!”于是执意完成了这件事。天河面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河水的腥气混杂着冤魂的悲鸣,两岸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不吓得双腿发抖。)
天灵帝纪:
天灵帝,讳丑女,厉帝弟也。母德妃,以帝诞时胎位逆,弗爱之,不乳。帝幼,以猪乳活。及长,出为逾地藩王,逾地贫窭,鲜少恩顾。
厉帝崩,无嗣,帝入继大统。性怪诞,耽于异癖,常与猪圈花猪交合,盖其幼所乳之畜也。帝宠之甚,欲废皇后,立花猪为后。御史大夫李璇固争,以举家自缢相胁,帝乃止。
一日,帝携花猪,与宰相萧刨卷乘花船游于江。刨卷家奴猝起,推花猪堕水。帝情急,忘己不习泅,跃水救之,遂溺死。(天灵帝,名丑女,是天厉帝的弟弟。他的母亲德妃,因为他出生时胎位不正,不喜爱他,不愿亲自哺乳。天灵帝幼年时,靠喝猪奶得以存活。等到长大成人后,他被分封到贫瘠偏僻的逾地做藩王,那里困苦落后,他也很少得到朝廷的眷顾与恩宠。天厉帝去世后,没有子嗣,天灵帝入宫继承皇位。他性情怪诞,沉溺于反常的癖好,常常和猪圈里的一头花猪交配,这头花猪正是他幼年时哺乳过他的那头猪。天灵帝对这头花猪宠爱至极,想要废掉皇后,立花猪为后。御史大夫李璇坚决反对,以全家自杀相要挟,天灵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一天,天灵帝带着花猪,和宰相萧刨卷一起乘坐装饰华丽的游船在江上游玩。萧刨卷的家奴突然起身,将花猪推入水中。天灵帝情急之下,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纵身跳入水中去救花猪,最终溺水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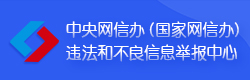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这不远坂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