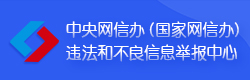我回了书院,却是少了个熟人,多了个“平青云”。依他所说,他是落榜的状元,是要登天的。我问他落榜的怎会是状元,他便不吭声了。他说门老爷子是他的扈从,要随他一同去山上享福,等教上五年书,就要回山下做官。
“平青云”的“心”很小,容易受着惊吓,又喜好记仇。可正是他的“心”太小了,吓了、恨了便忘了。办法总是多于困难的,他便找来纸笔,将仇恨记下。只是过上两日,记仇的纸笔也被他忘在脑后了。
“平青云”整日念叨着要回山上,也整日坐在门外等着他们来接他。门扈从也陪着他,一等就是好些日子。我是去问了的,前些年才考过一次,也确有个状元叫平青云,是要过两扇门登山、登云的。可那平青云是个青年,且不说早上了山,哪像他这般衰老。若是这么说来,他自不可能是平青云了。可平青云的魂好似附了他的身,反倒把“真正”的平青云落在这了。没人来接,他也就成了落榜的状元。
“平青云”有个师弟,姓什么宇文,据说是个大人物,能上山却不愿去,可羡煞他了。他捂着眼睛,呜呜哭着,说什么他这个师弟已经死了。哭着哭着又气红了脸,大骂着他的师父,说为什么不劝师弟上山。每当说到这里,他就要跳起来摔砸东西,对着门槛使劲踢去。踢痛了脚趾,又要躺倒在地大声惨叫。
坡下来了个汉子,身材矮小,瘦得病态,像是包了皮的骨头,头上裹着丧布,背着个竹篓。“平青云”还是很热心的,便向着他打听,问他来做些什么。汉子说了来历,是来找人的,找的是他从未见过的爹,他爹是在这里读书的,叫什么贾付收。“平青云”示意他坐下,唤来了门扈从,又叫来了我,让我俩找什么负心汉,叫什么贾付收。今天又要为汉子讨个什么公道,要将手下的知县叫来,为他审审这个案子。
“平青云”拍着汉子的肩,又自傲地笑,说着手下办事的利索,说着一定能给上满意的结果。“梁知县”来了,我站左边,门扈从站右边,将“梁知县”护在中间。“梁知县”也坐下了,问“平青云”要不要回家看看。“平青云”倒是果断,一口回绝了,说什么上山做官,却是不愿回那个家。
“梁知县”嘴皮子一张一合,汉子脸色不断变化,“平青云”却是听不真切,像是被鼓皮蒙了头,瓮声瓮气的,震得脑袋发懵。汉子怒视着“平青云”,两手像是钢钳,钳住了他的脖子,口中不断地咒骂,可没说出几句,却又哭了出来。没等旁人拉架,汉子便松了手,跪倒在地,掩面大哭,震得“平青云”头痛欲裂。
“平青云”从地上爬起,摇摇晃晃,朝着院外走去。再回首望去,只见“梁知县”成了宇文恒,“门扈从”是他的朋友,而我是他的师弟。我朝他呼喊着:“贾师兄!”他瞪大了眼睛,显然是没再听成“平青云”。可下一刻他撕烂了长衫,神色癫狂,哈哈大笑:“我是……平青云!”说罢,朝着岩山奔去,奋力一跃,便从悬崖坠入了林间。只听“哗啦”一声,便再无了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