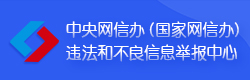夏末的雨总缠缠绵绵落个不停,巷口老槐树的浓绿被打湿,晕出深浅不一的墨色,映着杂货铺斑驳的木窗。沈辞守着这家传了两代的老铺,性子懒沉得像浸了水的棉絮,话少,整日就蜷在窗边的藤椅上,煮一壶温茶慢慢抿——他胃浅,喝不得凉的,温茶润喉又养人,翻几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旧书,日子淡得没半点波澜,连风穿堂而过,都带着慢悠悠的暖意。
雨下到第三日傍晚,门被轻轻撞开时,带进满股湿润的潮气,还有一道怯生生的身影。穿鹅黄蕾丝裙的人抱着鼓囊囊的布包,肩头沾着细碎的雨珠,乌黑的长发贴在颈侧,发梢滴着水,顺着白皙的脖颈往下滑。她眉眼软得像揉开的云,喘气时脸颊泛着浅红,声音糯糯的,带着几分无措的颤意:“抱、抱歉,雨太大了,能不能借避一会儿?就一小会儿就走。”
沈辞抬眼扫过她裙角磨得发毛的花边,又落回她攥得发白的指尖,声线懒哑得没什么起伏:“坐吧,桌上有纸巾。”说完便收回目光,继续盯着书页上的字,只是耳间多了道轻浅的呼吸声,混着窗外的雨声,细细软软的,竟不觉得扰,反倒添了点烟火气,熨帖得人心发暖。
对方慢慢挪到角落的凳子上坐下,动作轻得像怕踩碎地上的影子。她先小心翼翼擦了擦发梢的水,才慢慢打开怀里的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素色绸缎,还有几轴缠得紧实的绣线,最上面压着个木质绣绷,绷着半株没绣完的兰草,针脚细得像蛛丝,却透着股生涩的认真。指尖捏起银针时,能看见她指腹泛着淡淡的红,想来是绣了许久,被针磨出来的。
雨势没减,反而越下越密,砸在窗棂上噼啪作响。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轻轻蹙起眉,眼底漫过几分愁绪,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绣绷边缘,半天没落下一针。沈辞余光瞥见她紧抿的唇,见她浑身沾着雨气,指尖泛凉,沉默着起身,倒了杯温茶放在她面前的桌上,茶水冒着淡淡的热气,暖光映得她指尖泛粉。“喝点暖身子。”他声音依旧懒,却悄悄放柔了几分。
对方愣了愣,猛地抬眼望他,眼底闪着细碎的光,耳尖唰地红透,连忙低下头,小声道谢:“谢、谢谢你。”双手捧着杯子时,指尖轻轻抖了抖,小口小口喝着,温热的茶水顺着喉咙往下滑,驱散了身上的凉意,也悄悄暖了心底的局促。
雨停时,天已经擦黑了,晚霞漫过天边,染得云层泛着浅粉。她匆匆收拾好绣品,又低头道了次谢,才抱着布包慢慢往外走,裙摆扫过门槛时,留下一缕淡淡的皂角香,混着晚风飘进来,甜软得让人记挂。沈辞望着她纤细的背影消失在巷尾,才收回目光,指尖无意识碰了碰自己的杯沿,那里还留着点余温。
往后的日子,雨停了,她却总在傍晚时分来店里。有时穿浅粉的格纹裙,裙摆带着小小的褶皱,像是被精心熨烫过;有时是米白的碎花裙,上面绣着极小的雏菊,洗得发旧,却干净整洁。每次来,她都会先轻轻敲两下门,等沈辞应一声,才轻手轻脚走进来,依旧坐在角落的凳子上,安安静静刺绣。
沈辞渐渐习惯了这份固定的热闹。她来的时候,他会提前煮一壶温茶,刚好凑够两人的量;会特意在货架上添些素色的绣线,都是她常常用的浅蓝、乳白、淡青;夜里她绣得晚,他就把檐下的灯多开一会儿,暖黄的光透过窗,刚好落在她的绣绷上,也照亮她认真的眉眼。他依旧蜷在藤椅上翻书,只是翻页的速度慢了许多,偶尔会抬眼,看她低头刺绣的模样——长发垂落,遮住半张脸,阳光或灯光落在她发梢,镀着一层柔和的光晕,指尖翻飞间,绣线慢慢勾勒出花叶的模样,连呼吸都轻得怕惊着什么。
她也悄悄记着他的好。绣坏的小绣片,会被她剪成精致的碎花或小巧的叶片,趁沈辞不注意,轻轻放在他的书桌上;见他翻书时揉了揉眉心,就从布包里摸出一颗薄荷糖,悄悄放在他手边,声音轻得像风:“吃这个,能提提神。”雨天她会来早一点,帮着把门口的货物搬进屋里,怕沈辞懒动,淋着雨。
相处久了,她话渐渐多了些,偶尔会小声跟沈辞说些关于刺绣的事。说绣线要选软韧的,绣出来的花样才灵动;说不同的针法能绣出不同的纹理,兰草要用缠枝针,花瓣要用套针;说刺绣的时候要静下心,不然针脚就会歪歪扭扭。她说话时,眉眼弯弯的,眼底满是认真的光,声音糯糯的,像含着颗软糖,沈辞静静听着,偶尔应一两句,心底慢慢漫开几分柔软的甜。他本就随性散漫,却唯独对这份细碎的暖意上了心,会特意留意她喝茶的喜好,知道她不爱太浓的茶,就少放些茶叶;会记得她绣到某个时辰就会揉手腕,偶尔会递过一个小小的靠垫,让她垫着舒服些。
有一回午后,阳光正好,透过窗落在两人身上。她绣累了,就停下针,望着窗外的老槐树发呆,忽然小声问:“你会不会觉得,刺绣很无聊啊?”沈辞抬眼望她,见她眼底带着几分不确定,轻轻摇头:“不无聊,看着你绣,挺安心的。”她愣了愣,脸颊慢慢泛红,低头抿了抿唇,嘴角悄悄勾起一点浅浅的弧度,手里的针又动了起来,这次的针脚,比之前更稳了些。
秋意渐浓的时候,风里多了几分凉意,巷口的槐树叶慢慢泛黄,簌簌往下落,铺了满地细碎的枯黄。某个傍晚,几个拎着菜篮子的大妈说说笑笑走进店,刚要挑东西,目光扫到角落刺绣的她,瞬间收了声,眼神变得异样,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地飘过来:“你看那孩子,男不男女不女的,穿个裙子绣针线,像什么样子啊。”“就是啊,巷尾老李家的小子吧?好好的小伙子不学好,净搞这些娘们儿家的东西,他爸妈看见不得气疯。”“看着就别扭,没个阳刚气,以后谁敢跟他来往,丢死人了。”
窃窃私语像细针似的扎过来,她猛地僵住,手里的绣绷“啪”地狠狠摔在地上,绣线散落一地,银针滚到角落,素色绸缎被蹭得皱起,针脚处的线头松松散散,像她此刻慌乱的心。她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双手死死攥着裙摆,指节泛白得几乎要嵌进肉里,眼眶飞快泛红,滚烫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下唇不肯落下,头埋得极低,肩膀控制不住地剧烈发抖,连指尖都在颤,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脆弱得不堪一击。
沈辞皱起眉,之前的慵懒散意瞬间褪去,眼底沉得发冷,抬眼看向那几个大妈,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我的店里不兴背后嚼舌根,要挑东西就好好挑,不想挑就出去。”
大妈们愣了愣,没料到向来懒懒散散的沈辞会开口反驳,脸上有些挂不住,其中一个嘴硬道:“我们说句实话怎么了?本来就不正常……”
“正不正常轮不到你们评判。”沈辞打断她的话,起身一步步走到她身前,牢牢挡在她和大妈之间,身形不算高大,却透着让人不敢直视的强硬,“他在我这刺绣,安安静静不碍谁的事,你们要是看不惯,就别踏进我这店门。”
大妈们被怼得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撇着嘴骂骂咧咧地拎着菜篮子走了,出门时还不忘狠狠瞪了一眼,门被摔得砰响,震得货架上的罐头轻轻晃动。店里彻底静了下来,只剩她压抑的、细细的哽咽声,她蹲在地上,慢慢捡着散落的绣线,指尖抖得厉害,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砸在绸缎上,晕开点点湿痕,混着满心的委屈,狼狈又难过。
“我从小就跟着外婆学刺绣,外婆说我性子软,穿裙子绣活能静下心,我也喜欢这样,绣出来的东西,都是我用心做的……可他们总笑话我,说我不正常,说我丢人……”她哽咽着开口,声音发颤得几乎不成调,抬头望向沈辞时,眼底满是破碎的不安与惶恐,“你、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很奇怪?会不会也嫌弃我?”
沈辞蹲下身,慢慢帮她捡着绣线,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发顶,动作温柔得像怕碰疼她,声音放得极软,却带着无比的坚定:“不奇怪,一点都不。喜欢就去做,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更不用觉得丢人。在我这,你想穿什么、想绣什么,都可以,没人能说你,更没人能欺负你。”
她愣了愣,眼泪掉得更凶,像断了线的珠子,却慢慢往沈辞身边靠了靠,额头轻轻抵在他的肩头,双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角,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压抑许久的委屈终于彻底宣泄出来,哭声渐渐大了些,带着撕心裂肺的难过,却也慢慢多了几分安心。沈辞没说话,只是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慢慢安抚着,暖黄的灯光落在两人身上,映着满地散落的绣线,却格外温柔。
从那以后,她没再躲躲闪闪,依旧穿着喜欢的软裙来店里刺绣,眉眼间少了从前的局促与胆怯,多了几分坦然与自在。沈辞也总会护着她,若是再有街坊来店里说闲话,不等对方多说两句,就会被他冷冷赶出去,久而久之,没人再敢来扰,杂货铺成了她最安稳的避风港。
日子依旧慢悠悠地过,杂货铺里满是安稳的甜。她刺绣时,沈辞会悄悄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不说话,就静静看着她指尖翻飞,看她认真时轻轻咬唇的模样,看她绣出一朵花、一片叶时眼底闪过的欢喜。偶尔她的绣线缠在了一起,他就伸手帮她理顺,指尖偶尔碰到她的手,两人都会顿一下,脸颊慢慢泛红,空气里漫开淡淡的甜意。她绣累了,就靠在藤椅上歇会儿,头轻轻枕着沈辞的胳膊,软发蹭过他的手腕,带着淡淡的皂角香,暖得人心发颤。沈辞会给她递上一块甜糕,看着她小口吃着,眉眼弯成月牙,心底满是柔软的满足。
入秋后的第一场冷雨落下时,风卷着雨丝狠狠砸在窗上,天色沉得像泼了浓墨,巷口的槐树被吹得枝桠乱颤,枯叶混着雨水簌簌往下落,铺了满地湿冷的狼藉。她来店里的脚步慢了些,衣角沾着泥点,眼底带着化不开的愁绪,指尖攥着绣线,连针都穿了好几次才穿上。绣到中途,她忽然停下动作,指尖微微发颤,沉默了许久,才慢慢开口:“外婆病重,在城郊住院,我要过去照顾她,可能……可能很久都不能来店里了。”声音压得很低,带着难掩的哽咽,尾音轻轻发颤,眼底的泪意藏不住,慢慢漫了上来。
沈辞抬眼望她,见她泛红的眼眶映着窗外的冷雨,脸色也透着几分苍白,心底轻轻一沉,却还是温柔地看着她:“好好去照顾外婆,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她点点头,用力眨了眨眼,把眼泪逼回去,从布包里拿出一件叠得整齐的墨色披风,递到沈辞面前,披风上绣着漫天细碎的星子,针脚密密麻麻,每一针都藏着无数个夜晚的心血。“这是我绣的,送给你。天冷了,穿这个能暖和点。”她声音发颤,抬手轻轻碰了碰沈辞的指尖,微凉的触感一碰就收,“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护着我,我……我会很想你。”
沈辞接过披风,指尖触到细腻的绸缎,还有上面残留的她的温度,心底暖得发疼,他抬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认真地说:“我等你回来,店里永远留着你的位置,檐下的灯,也永远为你开着。”
她用力点头,眼泪终究还是没忍住,顺着脸颊滑落,砸在披风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咬着唇挤出一个浅浅的笑,慢慢收拾好自己的绣品,布包被攥得紧紧的,一步三回头地往外走。冷风裹着雨丝扑在她身上,裙摆被吹得轻轻晃动,单薄的身影在昏沉的天色里慢慢走远,最后消失在巷尾的雨幕中,只留一缕淡淡的皂角香,混着湿冷的雨气,久久散不去。沈辞站在门口,望着她离去的方向,手里紧紧攥着那件星子披风,指尖传来绸缎的暖意,心底却空落落的,冷雨打在脸上,凉得刺骨。
之后的日子,又回到了最初的安静,却少了份往日的淡然,多了份满心的牵挂。沈辞依旧蜷在藤椅上煮茶翻书,只是每天都会提前煮一壶温茶,放在角落的桌上;檐下的灯,每晚都会多开许久,暖黄的光映着空荡的角落,像是在等着什么人归来。他把那件星子披风挂在藤椅旁,偶尔会摸一摸上面的绣线,想起她认真刺绣的模样,想起她糯软的声音,想起她泛红的耳尖,心底的甜意就会慢慢漫开,驱散所有的孤单。
日子一天天过,槐树叶落尽了,寒风起了,最后一场秋雨过后,冬雪悄悄落下。巷口被白雪覆盖,一片洁白,老槐树的枝桠上积着雪,像是开了满树的白花,天地间静得只剩雪花飘落的簌簌声。沈辞坐在店里,煮着一壶温茶,水汽袅袅升起,模糊了窗玻璃上的霜花,他望着窗外茫茫的雪景发呆,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藤椅旁的星子披风,心底的牵挂像雪一样,越积越厚。
忽然,门口传来轻轻的叩门声,很轻,却在寂静的雪天里格外清晰,打破了满室的沉寂。沈辞愣了愣,这个时辰,很少有客人来,他慢腾腾起身去开门,冷风裹着雪意瞬间涌进来,让他忍不住缩了缩肩。抬眼的瞬间,他却猛地顿住,眼底满是错愕与惊喜,连呼吸都慢了半拍。
雪地里,站着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她穿着一条米白色的软裙,外面套着一件浅灰的薄外套,长发上沾着细碎的雪花,睫毛上也凝着点点白霜,却衬得眉眼愈发清亮,眼底闪着细碎的星光,正朝着他浅浅笑着,像一束暖光,撞碎了漫天风雪的清冷。“我回来了。”她笑着开口,声音依旧糯软,带着几分雀跃,还沾着点雪后的清冽,轻轻落在沈辞心底。
沈辞望着她,许久才缓过神,心底的空落瞬间被填满,暖意顺着四肢百骸漫开,连冻得发僵的指尖都慢慢热了起来。他慢慢笑了,眼底褪去了往日的慵懒,满是温柔的光亮,伸手轻轻帮她拂去发梢的雪花,指尖触到她微凉的脸颊,又连忙收回手,拉着她快步走进店里,关上门牢牢挡住寒风。暖黄的灯光落在她身上,雪水顺着发梢慢慢滑落,她抬手揉了揉冻得发红的鼻尖,眉眼弯成了月牙,眼底满是藏不住的欢喜。
沈辞给她倒了杯滚烫的温茶,递到她手里,看着她捧着杯子呵气暖手的模样,心底满是失而复得的安稳。她喝了口茶,暖意顺着喉咙漫进心底,抬头望向沈辞,笑着晃了晃手里的布包:“我绣了好多新花样,有冬日的雪梅,还有巷口的老槐树,以后,就能一直在这里绣了,再也不离开了。”沈辞用力点头,抬手轻轻揉了揉她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轻声的“好”。
檐外的雪还在下,簌簌落着,染白了整个世界;檐内的灯暖得人心发颤,温茶的香气漫满全屋。她坐在熟悉的角落,慢慢打开布包,绣绷落在桌上,银针穿梭间,绣线慢慢勾勒出冬日的雪景,也绣着两人往后绵长安稳的时光。沈辞蜷在藤椅上,静静看着她,目光从未离开,温茶的暖意漫在心底,日子慢而甜。后来开春,老槐树抽了新芽,巷里风暖,沈辞把杂货铺的木门换了新,檐下挂了串她绣的碎花风铃,风一吹就叮当作响。他不再只蜷在藤椅上,会陪着她选绣线、描花样,指尖相触的暖意岁岁常存,两人守着这家小店,伴着绣影与茶香,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最安稳的归宿,岁岁年年,岁岁相依。
绣香伴温常
暮色漫过巷口老槐树时,林絮攥着绣绷往杂货铺走,米白裙角扫过落满枯叶的石板,风卷着细碎凉意缠上脚踝,怀里素绸裹着未绣完的兰草,针脚藏着难掩的欢喜,连叔父身后追来的斥骂,都压不住指尖触到绸缎的雀跃。他性子怯软,习惯把情绪藏在心底,连喜欢的绣活都不敢光明正大做,唯有沈辞的杂货铺,能让他卸下防备,安安稳稳待上许久。
杂货铺的暖灯总亮得准时,推开门的瞬间,清浅茶香漫过来裹住满身寒气,沈辞蜷在藤椅上翻书,指尖捏着书页轻缓翻动,眉眼疏淡间带点漫不经心的懒。他性子散漫惯了,日子过得随性,从不多管旁人闲事,却偏偏对林絮多了几分在意。初见时只觉这少年眉眼干净,攥着绣绷的模样带着股执拗的软,久而久之,倒渐渐记挂起他的一举一动——记着他怕茶浓,煮茶时特意少放些茶叶;记着他绣活久了会揉手腕,悄悄找软棉缠好绣绷;记着他爱吃镇上的桂花糕,寄卖绣品回来总会绕路带一块。他自己都没察觉,原本清静的日子里,多了份盼着少年来的隐秘心思,见他推门进来,心底便会漫开细碎的暖意,连翻书的动作都慢了几分,余光总忍不住往角落瞟,看暖灯落在他发梢的柔光,看他专注刺绣时轻蹙的眉尖,看他偶尔抬头时眼底藏不住的怯意与明亮。
见林絮来,沈辞抬眼瞥了一眼,没说话,只是往角落推了推那张磨得温润的木凳,转身倒了杯温茶放在桌沿,杯壁凝着细薄水汽,暖光映在上面,漾开细碎的亮。林絮轻声道了谢,坐下时把绣绷摆稳,银针穿线的瞬间,心底的慌意便顺着针脚慢慢沉了下去。他偷偷抬眼望沈辞,对方垂着眼翻书,侧脸线条柔和,浅棕的瞳仁映着暖灯,温柔得让人心尖发烫,赶紧低下头,指尖捏着针,耳尖悄悄泛红,针脚都慢了几分。
起初相处,两人难免有磨合的小磕碰。沈辞习惯了独处清静,林絮绣活时虽安静,却总因紧张弄出些细碎声响——穿线时银针掉在桌上的轻响、整理绣线时绸布摩擦的动静,偶尔还会不小心碰倒茶杯,溅湿桌角。有次沈辞正看得入神,被林絮打翻茶杯的声响惊到,下意识皱了眉,语气带了点不耐:“慢些弄,别毛手毛脚的。”林絮瞬间涨红了脸,连忙拿纸巾擦拭,指尖慌乱得发抖,连声道歉,往后好几天都放不开手脚,绣活时格外拘谨,针脚都失了往日的灵动。沈辞察觉到他的局促,心里满是愧疚,夜里翻书时总想起少年泛红的眼眶,越想越不安,后来见他再碰倒东西,不再皱眉斥责,只是默默递过抹布,轻声说“没事,擦干净就好”,连翻书的动作都下意识放轻,怕再惊到他,慢慢学着包容他的小笨拙。
林絮也悄悄记着沈辞的喜好与习惯。知道他怕吵,便刻意放轻所有动作,穿线时低头凝神,整理绣线时轻轻拉扯,连呼吸都压得浅浅的;见他茶杯空了,便轻手轻脚拿起茶壶添满温水,动作轻得像怕惊散满室的静;沈辞偶尔咳嗽,第二天他便悄悄带些晒干的陈皮来,放在他茶罐旁,夜里偷偷查了陈皮煮茶能润喉,隔天见沈辞煮茶时添了两片,抬眼冲他淡笑,眼底软得像化了的糖,他便偷偷欢喜了好久。沈辞看在眼里,心里愈发柔软,见他绣到半途揉手腕,便主动走过去帮他揉一揉,指尖触到他微凉的皮肤,两人都顿了一下,各自移开视线,耳根悄悄发烫,屋里的茶香仿佛都浓了几分。
日子久了,两人间的暖意越积越浓,沈辞愈发在意林絮,见他被巷里的闲言碎语扰得低落,总会慢悠悠起身,往门口站一站,懒声说句“看够了就走,别在这扰人”,语气平淡却带着威慑力,把杂音都挡在门外。夜里见林絮对着绣绷发呆,便坐过去陪他煮茶,没说太多话,只是安静陪着,暖烟袅袅缠着凉光,看少年慢慢平复心绪。他喜欢看林絮专注刺绣的模样,喜欢看他吃到桂花糕时弯起的眉眼,喜欢看他悄悄关心自己时的小心翼翼,这份心思藏在心底,越沉越暖,连自己都没察觉,早已离不开这份满是绣香的日常。
林絮对沈辞的心意也渐渐藏不住,从最初的感激,慢慢变成了满心的欢喜。他喜欢沈辞慵懒却温柔的模样,喜欢他默默护着自己的坚定,喜欢他记得自己所有小喜好的细心。每次绣活时,目光总会不自觉往沈辞身上飘,看他翻书、煮茶,哪怕只是安静坐着,都让人心安。可这份喜欢里,藏着深深的惶恐——他是男生,却总穿着素雅的衣裙,靠着伪装才能留在这方小天地,留在沈辞身边。他无数次在夜里辗转,指尖摩挲着绣绷上的针脚,反复琢磨沈辞的眼神,怕身份拆穿的那天,沈辞会厌恶、会疏离,连这仅有的温暖都会失去。这份心理斗争像根细刺,扎在心底,越疼越不敢表露,连偶尔与沈辞对视,都忍不住躲闪,怕眼底的慌乱泄露了秘密。
两人的磨合藏在日常琐碎里,慢慢磨出了默契。沈辞散漫随性,做事不拘小节,杂货铺的货架总摆得有些杂乱,东西用完随手乱放;林絮心思细腻,爱干净讲条理,见不得杂乱,便趁沈辞不注意,悄悄整理货架,把货物分类摆好,把用过的东西归回原位。起初沈辞找东西时总找不到,难免有些烦躁,语气带了点冲:“我放哪不用你管,别瞎收拾。”林絮被他说红了眼,却没反驳,只是往后整理时,会默默记好沈辞常用东西的摆放位置,尽量不打乱他的习惯。沈辞渐渐发现,货架整齐后找东西更方便,屋里也清爽了许多,心里渐渐认可了林絮的细致,后来见林絮整理,会主动递过抹布,偶尔还会跟着一起收拾,笨拙地学着分类,慢慢改掉了自己不拘小节的毛病,连煮茶时都会记得多倒一杯温着,等林絮绣累了喝。
叔父的出现,终究撞破了所有伪装。那天叔父堵在杂货铺门口,脸色阴沉如墨,一把扯掉林絮耳边的发夹,长发散落下来,他指着林絮嘶吼:“你就是个男的,装女的骗人为乐,不嫌丢人!”
林絮浑身僵住,血液像瞬间凝固,脸色惨白如纸,指尖死死攥着裙摆,指节泛白,浑身控制不住地发抖。羞耻、恐惧、绝望一股脑涌上来,他死死低着头,不敢看沈辞的眼睛,眼泪砸在绣绷的素绸上,晕开深深浅浅的痕。他脑海里全是胡思乱想,沈辞会不会觉得被欺骗?会不会觉得他怪异恶心?会不会从此再也不让他踏进这家店?那些藏在心底的欢喜,此刻全变成了尖锐的刺痛,连呼吸都带着疼,指尖的绣针掉在桌上,发出轻响,却没力气去捡。
沈辞却只是皱了皱眉,眼底没有半分意外,更没有厌恶,只有对叔父撒野的冷意。他上前一步,稳稳将林絮护在身后,抬手隔开叔父还要上前的动作,语气沉得没半点温度:“闹够了就滚,别在这烦他。”叔父骂他被蒙在鼓里还帮着骗子,沈辞全然没理会,目光落在身后发抖的身影上,语气瞬间软了下来,轻轻说:“过来,别怕。”
林絮愣了愣,迟疑着往前挪了半步,依旧不敢抬头。店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的心跳快得要炸开,哽咽着开口,声音破碎又卑微:“我……我骗了你,我是男生,你要是觉得不舒服,我……我现在就走,再也不打扰你。”
沈辞转头看他,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动作温柔又沉稳,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我知道。”
林絮猛地抬头,眼里满是震惊,眼泪还挂在脸上,满脸难以置信。
“早看出来了。”沈辞收回手,倒了杯温茶递给他,杯壁的暖意顺着指尖漫进来,他语气依旧平静,没有多余的情绪,却字字戳进林絮心里,“我在意的从来不是你穿什么、是男是女,是你这个人,是你待我的心意,其他的都不重要。”
简单的一句话,像暖流瞬间冲散了林絮心底所有的惶恐与不安,他盯着沈辞浅棕的瞳仁,里面干净又真诚,没有半分嫌弃与疏离,只有稳稳的笃定。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这次却带着卸下重担的轻松,还有满心的暖意,他攥着温热的茶杯,终于慢慢稳住了发抖的身体。
往后的日子,暖灯依旧夜夜长明,茶香裹着绣线的清润漫满全屋。林絮渐渐放下所有心结,不再刻意掩饰,却依旧喜欢穿素雅的衣裙,绣喜欢的花,眉眼间多了从前没有的坦然与自在。他绣得更勤了,从兰草、山茶到巷口的老槐树,针脚愈发细腻精湛,镇上越来越多人喜欢他的作品,裁缝铺主动找他合作,连巷里曾经碎嘴的大妈,都主动上门求他帮忙绣嫁妆纹样,闲言碎语渐渐消散在日常里。
沈辞依旧保持着散漫的性子,却总把林絮的事放在心上,会悄悄记下他常用的绣线颜色,在货架上慢慢添齐;会在他绣到深夜时,端来一杯热姜茶,帮他揉一揉酸胀的肩膀;寄卖绣品回来,总会绕路带块他爱吃的桂花糕,偶尔还会带些质感上乘的绸缎,轻轻放在桌上:“试试新料。”两人闲时便一起整理货架、晾晒绣品,傍晚伴着暮色在巷里散步,风卷着槐香裹住两人的身影,不用多说太多话,并肩走着就格外安稳。
心底的喜欢再也藏不住,在一个月色温柔的夜晚,林絮绣完最后一针山茶,把小巧的绣片轻轻放在沈辞面前,指尖攥着裙摆,声音轻而认真:“沈辞,我喜欢你,想一直跟你守着这家店,岁岁都在一起。”
他说完便紧张地垂着眼,沈辞低头看了眼绣片上鲜妍的花瓣,抬眼时眼底漾着浅淡的暖意,伸手轻轻牵过他的手攥紧,指尖温热有力,喉间落下一个轻而沉的字:“好。”
暖灯映着两人相握的手,茶香与绣香缠在一起,漫过朝朝暮暮,温柔又绵长,往后岁岁,皆是安稳常伴,情意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