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无罪论的终结与责任伦理的兴起
一、导论与问题界定
“技术无罪论”(亦称“技术中立”)主张技术本身不承载价值,善恶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这一观念在1984年索尼案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中获得里程碑式支持,并长期影响互联网与知识产权法。然而,进入平台社会与算法时代后,技术不再仅是“工具”,其架构、默认与规模效应系统性塑造行为与社会秩序,司法与伦理层面对“中立”的容忍急剧收缩。典型如2016年快播案引发“技术无罪”与“红旗原则”的全民辩论,官方评论明确指出“技术本身并不是谁的免罪牌”。本文认为,在功能、责任与价值三维上,“技术无罪论”已失去规范与事实基础,必须让位于以“可预见性—可控制性—可归责性”为核心的责任伦理与治理框架。
二、法理转折与司法立场
“技术中立”在法理上至少包含三重意涵:功能中立、责任中立与价值中立。早期以“工具理性”为据,强调产品功能与其社会后果可分离;但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与云存储等技术使“功能—后果”高度耦合,平台对内容分发、缓存与可见性具有实质控制力,“菜刀论证”难以成立。司法上,避风港原则并非护身符,面对“显而易见”的违法或侵权(红旗),提供者负有积极注意义务;在快播案等裁判中,法院以“技术背后的责任与意图”为关键变量,否定以“技术无罪”免责的路径。法理由此从“工具—后果分离”转向“可预见—可控制—可归责”的归责结构,宣告“技术无罪论”的司法破产。
三、技术—资本—劳动的再分配效应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外生变量”,其“资本主义应用”会改变分配格局与劳动关系。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中指出: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在既定工作日下,资本以技术为手段推动“工资下降—利润上升”的结构性再分配,并带来工人与机器的历史性对立。这一分析揭示:技术并非“无辜的器具”,其在特定生产关系下具有明确的价值负荷与分配后果。20世纪以来,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揭示“工具理性”与“技术意识形态”对主体与社会的塑形,技术—资本的结合成为现代社会支配结构的重要来源。由此,“技术无罪论”在事实层面被证伪:技术以制度与资本为中介,持续参与社会权力的生产与再分配。
四、哲学与伦理的终局论证
当代技术哲学进一步瓦解“技术无罪”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汉斯·约纳斯提出“责任伦理”,强调面对具有巨大力量与不可逆后果的现代技术,人类须对自然与未来承担“可预见性—可避免性—可补救性”的义务;传统以“人是目的”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伦理已不足以约束“普罗米修斯的羞愧”所揭示的人—技失衡。贝尔纳·斯蒂格勒以“技术作为记忆的外在化”与“一般器官学”说明技术构成人类的“第三持存”,既开启新的个体化,也带来依赖、异化与操控的药理效应。与此同时,兰登·温纳的“自主性技术”警示大型技术系统呈现脱离个体意图的运行逻辑,迫使社会以制度与伦理进行“前置约束”。这些思想共同指向:技术不是中性的“器物”,而是嵌入制度、文化与未来的价值—权力—责任综合体,因此“无罪”之辩在规范与存在论上均难以成立。
五、治理路径与行动框架
将“技术无罪论”送入历史,不是否定创新,而是以制度化的责任引导创新。第一,确立“价值敏感设计”与“算法可解释/可审计”的工程伦理底线,将歧视、成瘾、隐私侵害等风险纳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前置评估。第二,完善“红旗—避风港”的精细化适用:对显而易见的违法内容、系统性侵权与高危算法,建立强制合规与连带责任;对难以预见的风险,以“安全港+尽职合规”激励治理创新。第三,以“可归责性”重构平台义务:明确内容治理、数据治理与模型治理的注意义务、记录义务与纠错义务,以“可预见—可控制—可补救”为三要素设置责任梯度。第四,强化跨学科审查与公众参与:在医疗AI、基因编辑、预测性警务等高风险场景,引入伦理审查、外部审计与公民陪审。第五,推动国际协同与行业自律: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协调跨境平台治理与标准制定,避免“竞劣”与“监管套利”。唯有以责任伦理为纲、以制度设计为目,技术才能从“失控的力量”转化为“可治理的公共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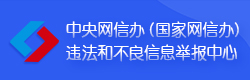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技术无罪,建立在技术,还是工具的基础上,建立在解决问题的根本上,但如果本质上偏移,那么技术就不再是中性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