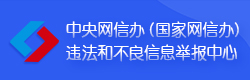李雨生正坐在道观外,昏沉的准备睡去,忽然传来一声重物撞门的巨响,震得李雨生一个激灵,瞬间清醒过来。他攥紧枪杆,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道观深处炸开何元破了音的嘶吼:
【跑!菊待开你快跑!】
话音未落,道观的侧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一道人影连滚带爬地扑了出来,正是菊待开。他像只被野狗撵着的兔子,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在院中的青苔上,连头都没抬,径直朝着拴马的树冲去。
李雨生心头一紧,跨步上前想拦他,问道:
【公子,出什么事了?何元呢?】
可菊待开像是没听见,疯了似的推开他,直奔马匹而去,眨眼间,菊待开已经翻身上马,连缰绳都没系稳,就狠狠一鞭抽在马臀上。
骏马长嘶一声,四蹄翻飞,驮着他朝着林莽深处狂奔而去,扬起的尘土呛得李雨生直咳嗽。同时眼角的余光里,道观的侧门阴影处,缓缓踱出一道人影。
不是何元。
是丁伶子。
她的晚好的半边脸覆在黑暗里,但毁坏的另外半张脸则照耀在月光下,她的手里拖着什么人,那人软塌塌的,四肢随着她的脚步晃荡,头部似乎少了什么东西,不断的流出血来。
李雨生看见丁伶子的指尖嵌在那人的的衣领里,力道不大,却像拎着一只小鸡,她手腕轻轻一扬,那人被丢在李雨生的脚边,温热的血溅在李雨生的靴面上,顺着靴筒往上渗。
李雨生低头,目光撞在脚边那具软塌塌的躯体上,是何元,他的头顶空荡荡的,因为头盖骨不知去向,暗红的脑浆糊了满脸,那双平日里总是不高兴的眼睛,此刻瞪得浑圆,里头还残留着没散尽的恐惧,死死地盯着天。
不远处,丁伶子从台阶上走下来,她仅剩的那只眼睛已经布满的愤怒的血丝,只是恨,只是怨气罢了……吗?
不,还有妖気,不是妖怪身上的那种妖气,而是和素蛇相同的,妖気。
【丁伶子】“菊待开在哪里。”
李雨生后撤一步,把腰间的双生枪组合成了一把红缨长枪,枪尖斜指地面,脸上再无半分方才的昏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紧绷的凝重。
李雨生喉结滚动,声音因为过度紧张而有些口齿不清道:
【公子已经骑马跑了!你追不上他的。】
丁伶子听到这话,脚步停在台阶上。
这沉默来得突兀,却比雷霆怒吼更令人心悸。李雨生握着红缨枪的手心早已被冷汗浸透,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一下下撞在胸腔里,震得耳膜生疼。他知道,眼前这女子早已不是昔日那个娇柔的丁家小姐,她身上那股可怕显然远超常人。
忽的,丁伶子笑了。
那笑声极轻,却带着一股彻骨的邪意,像是九幽之下的鬼魅,在暗夜中低低回荡。她半边脸的肌肉因为腐烂而扭曲,笑起来时,嘴角扯出一道极不自然的弧度。
【丁伶子】“追不上?这可说不准,他诺逃的了一时,那我就追杀他一世,天涯海角总会被我碰上,我现在有的是时间,菊待开如果死在我的前面,我就挖了他的尸骨,打烂他的坟墓。”
【丁伶子】“对了…在那之前,你要不去陪陪何元?”
话音未落,丁伶子身形陡变!
她原本立在台阶之上,与李雨生尚有丈许之遥,可这一言方毕,竟似一只金雕般掠下台阶,顷刻间人已欺至李雨生面前。这等速度,竟如鬼魅附体,全无半分常人该有的滞涩,直看得李雨生心头一寒。
生死关头,哪敢有半分迟疑?李雨生双臂猛振,将那杆红缨长枪舞得虎虎生风,枪尖划破夜色,带起一道锐啸,直刺丁伶子心口要害。这一枪功力非常,端的是又快又狠,乃是他压制近身的枪法。
不料丁伶子不闪不避,竟侧身微微一拧,那柄寒光闪闪的枪尖便擦着她的衣襟掠过,只差分毫,便能洞穿她的躯体。李雨生心头一惊,正待回枪横扫,却见丁伶子的手已然抓来。
李雨生急忙收枪格挡,枪杆与手掌相撞,他只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力涌来,迅速连退三步,方才稳住身形,抬眼再看,丁伶子竟依旧立在原地。
他不敢再有半分小觑。牙关紧咬,周天内真气急转,伴随一声怒喝,手中红缨长枪霍然展开,一式“尾断松躯”,带着破风锐响,朝着丁伶子拦腰扫去。这一枪蕴含着他七成的功力,枪缨猎猎飞舞,声势骇人。
可丁伶子确是从容,她居然敢徒手抓住李雨生横扫而来的枪头,伴随着骨头断裂的声音,李雨生本以为丁伶子的手骨会因为硬接而彻底裂开,然而丁伶子却像是没事般,抓着李雨生的枪头连人带枪的丢去。
李雨生落地重新稳住身形,继续刺枪攻击而去,两人的身影,在道观院中飞速缠斗。枪尖擦过廊柱,粗壮的木柱应声断裂,轰然倒地;掌风扫过供桌,木桌瞬间四分五裂,木屑纷飞。
两人身影起落,高速的死斗夜色里交织成一片密不透风的网,竟是硬生生斗了五六十回合,难分高下。
又是一记硬拼,二人各退几尺,再看周遭,哪里还有半分道观的模样?只剩下遍地的瓦砾木屑。
两人分立在废墟两端,目光死死锁定对方。
李雨生知道,方才五六十回合已是自己的极限,真气消耗巨大,再斗下去,必败无疑。
他越想越是心惊,越想越是疑惑。
方才那五六十回合的缠斗,他看得真切,丁伶子的招式路数,粗疏得很,拳脚之间毫无章法,顶多算得上三流水平,别说什么精妙武学,连基础的身法都透着一股子野路子的笨拙。可偏偏就是这样的招式,配上她那副异于常人的躯体,竟硬生生扛住了自己的猛攻!
即使丁伶子的武功水平只有三流普通,但她的速度、力量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没怎么用真气或者内力,仅靠着碾压式的肉体强度就能让自己的实力达到二流顶峰!
这就是所谓的力大飞砖吗。
方才自己一记“下棍式”,枪杆重重砸在她肩头,换作寻常武人,早该骨断筋折,倒地不起,可她竟只是闷哼一声,反手就拍出一掌,按照常理来说,丁伶子不是应该整只手都动不了吗。
不过,三流的招式,二流顶峰的实力,说到底,还是差了一截。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一流!
方才五六十回合的缠斗,不过是他试探虚实,亦是真气消耗下的权宜之计。真要论起真正的绝技,眼前这半人半鬼的怪物,根本接不住他全力一击!
李雨生深吸一口气,血管里的气血渐渐平复,全身的真气开始疯狂涌动,汇聚于周天,再顺着经脉,源源不断地涌向手中的红缨长枪。枪杆发出低沉的嗡鸣,似如龙游。
他准备用自创的那式一枪破千军。
那是足以击碎十几万斤巨石的杀招,枪出如龙,快如闪电,枪尖所过之处,万物皆摧!
丁伶子的速度再快,肉体再强横,又岂能躲得过这一招?
丁伶子瞧着李雨生周身的真气越来越盛,那杆红缨长枪震出低沉的嗡鸣,心头竟浮起一丝莫名的烦躁。
这人怎么还不出招?
磨磨蹭蹭的,是在蓄力,还是在盘算什么阴诡伎俩?
她的脚无意识地碾着脚下的瓦砾,想着只待李雨生枪尖一动,便要再度扑上去,以力破巧。
可这念头刚落,李雨生动了。
他猛地沉腰扎马,双臂青筋暴起,周身的真气轰然炸开,卷起漫天尘土。那杆红缨长枪在月光下划过一道极致的弧光,枪尖的寒光骤然暴涨,竟似化作了一条吞吐着山河的怒龙!正是李雨生的成名绝技,一枪破千军!
枪出闪电,快得超乎想象,竟是比丁伶子的身法还要快上三分!
丁伶子想也不想便侧身疾闪,她的速度已是极致,身形化作一道黑影,堪堪要避开枪尖的轨迹,可那枪尖,竟像是长了眼睛,提前预判了她闪避的方向,枪尖一偏,带着破风的锐啸,精准无比地,刺进了她的心脏!
丁伶子的动作僵在半空,低头看着胸口那截没入的枪尖,与此同时,枪尖余势未绝,竟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道,朝着她身后的树林怒射而去!
“轰隆——”
震天动地的巨响炸开,气浪狂飙,毁天灭地。
那片茂密的树林,竟在这一枪的余威之下,被硬生生夷为平地!断木残枝飞射四方,地面上赫然出现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月光洒落,沟壑里一片狼藉,再无半分生机。
死寂。
废墟之上,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风卷着尘土,掠过断壁残垣,发出呜呜的声响。
丁伶子的独眼里,终于浮起了一丝难以置信的错愕。
原来这就是一流真正的实力吗,哪怕李雨生连一流好手都算不上,却有着如此恐怖的实力。
她缓缓抬头,看向李雨生那张紧绷的脸。
黑红色的血,从丁伶子的嘴角溢出。
李雨生盯着刺入丁伶子胸口的枪尖,他手腕发力,想将长枪抽回,这一击既中,说明他已经彻底了结这个怪物。
可那枪杆竟纹丝不动,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咬住了。
对面呼吸的气息扑在他汗湿的脸上,李雨生心头一沉,低头望去,只见没入丁伶子身体的那半截枪身,竟正被不断翻涌的血肉缓缓包裹。那些还在渗着黑红血液的创口,像是有了生命一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愈合,丝丝缕缕的筋肉缠上枪杆,将冰冷的铁箍得密不透风。
被这具本该死去的躯体,用疯狂自愈的血肉,把枪头牢牢地锁在了心脏里。
李雨生正攥着枪杆,拼尽全力想要抽出那截被血肉锁住的铁枪。忽然,一股恐惧感拼命的警告,只见丁伶子那只布满血丝的独眼里,哪还有半分错愕?只剩下一片浓稠得化不开的怨毒。
丁伶子抬起手,精准无比地掐住了李雨生的脖颈,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只手的力道,像是钢钳般收紧,空气被硬生生掐断,窒息的痛苦瞬间屏蔽了剩下的真气。
他疯了似的挣扎,双腿拼命蹬着地面,另一只手胡乱抓着,用指尖抠进丁伶子手臂的皮肉里,可那些被抠开的伤口,竟在指尖下飞速愈合,连一丝血都没再渗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她还活着?
心脏明明被刺穿了,为什么……
李雨生的挣扎越来越微弱,力气开始削弱,双腿也软了,视线开始模糊,耳边的嗡鸣越来越响,道观废墟的轮廓、月光的惨白、丁伶子那可怕的面容,都在渐渐消散。
他能感觉到,生命正顺着被掐紧的脖颈,一点点流逝。
最后,他的手彻底垂落,身体“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丁伶子将李雨生的尸体丢到了何元的旁边,她垂眸看着胸口那截枪杆,双手扣住枪杆,开始发力,皮肉被撕裂,表情有些痛苦,牙关紧咬,每往外拔一寸,都有新的血肉被铁枪带起,创口像一张咧开的嘴,不断溢出血液,却又在极快地蠕动、粘合。
终于,长枪被她从胸口拔出,枪尖上还挂着丝丝缕缕的血肉,丁伶子捂着胸口的伤口,努力站直身子。那处被洞穿的地方,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自愈,最后竟连伤疤都没有。
她转头,看向林莽深处的方向,独眼里的怨毒重新燃起,正要迈步追去,可脚踝到大腿根部瞬间丧失了力气,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倒了下去。
丁伶子用手撑着地面,大口大口的喘气,感到一股剧烈的窒息感猛地攫住了她,每一次吸气,都带着肺叶被撕裂般的剧痛,嘴里狼狈的喷着血,糊了整个满下巴。
糟糕,方才那一枪,何止是洞穿了心脏。
自己的肋骨被全部震断,断裂的骨茬刺破了肺叶,导致大量的血液进入肺部堵住了呼吸;那股沛然莫御的真气,更是顺着创口钻进了她的头颅,使得眼前冒着金星,耳边嗡嗡作响,连视线都开始天旋地转,是脑震荡。
自愈的细胞正将断裂的肋骨修复归位,肺部作为主要脏器修复的比较慢,但是却无大碍了,但是心脏不一样,它被彻底的打散成百十八片,丁伶子几乎要重新再长一个心脏,让修复工作变得过于漫长。
再生所消耗的是大量的体力和精神力,但丁伶子不像素蛇,有难以撼动的精神,她不过是刚刚握住这份长生的门槛,连皮毛都未曾学会。如今这种情况下丁伶子居然还未昏厥过去就已经是奇迹了。
方才那场死斗,她靠着的是焚尽一切的恨意,是被怨毒撑起来的本能。恨意烧得最烈的时候,她感觉不到痛,感觉不到累,只知道扑上去,撕碎眼前的一切。可现在,何元以及李雨生的死,让那股支撑着她的恨意,骤然泄了大半。理智一点点回笼,疲惫便如同潮水般,瞬间将她淹没。
丁伶子咬着牙床,靠从牙缝中吸气来缓解疼 不行,不能昏。
菊待开还在逃。
她还有仇没报。
她一点点地,一寸寸地,从地上爬起来。
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脚踝的软麻感还没褪去,好几次都差点栽倒,只能死死攥着胸口的衣襟,吃力的往前走。
丁伶子咳得撕心裂肺,咳着咳着,眼前就晃过素蛇的脸。
若是素大哥还在,会不会……会不会告诉她,为什么心口的窟窿能长好,为什么断骨能重新接上,为什么明明疼得快要死掉,却偏偏死不了?
她不知道自己已经长生不老了,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早已被素蛇的血肉改造。她只觉得恐惧,觉得茫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认不出的怪物。
为什么,只有自己还活着,自己到底怎么了?
现如今,她只能拖着这具千疮百孔却又死不了的躯体,忽然觉得一阵铺天盖地的悲哀。
素大哥死了…和爹娘一样自己再也见不到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多远,丁伶子的脚步,早已没了章法。
那不是走,是挪,是拖,是一具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却还在凭着惯性往前蹭的躯壳。
她的体力,早就耗光了。
她的精神,早就垮了。
甚至连意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沉进了一片黑暗里。
她在心脏长好的那一刻意识就昏过去了。
可她还在走。
脑海里空空如也,像被大风刮过的荒原,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字,一个念头像野草般疯长,钻透了混沌的黑暗,从嘴挤出来,机械的念了一遍又一遍。
【丁伶子】“素大哥……素大哥……素大哥…求求你,不要让我一个人活着。”
忽的,一股猛力从侧面袭来,带着麻绳粗糙的勒感,狠狠缠上了她的腰部。
她根本来不及反应,甚至连一丝挣扎的念头都没来得及升起,整个人就被那股力道拽得往前一扑,重重摔在粗糙的土路上。额头磕在冰冷的石头上,虽然丁伶子的眼睛还是睁着的,但意识早就晕过去,所以对这点疼痛并无任何反应。
【嘿,这娘们儿看着半死不活的,倒还有几分姿色,咱明天把她卖到窑子去?】
原来她不知道甚么时候走到了一条商道上,夜正入深,人迹罕至,居然被两个骑马路过的马匪发现了。
丁伶子的眼皮动了动,她能感觉到有人蹲在自己身边,可她的意识,还沉在那片无边的黑暗里,像是被人用一块巨石压住了,怎么也醒不过来。
另一个马匪推了下同伴,语气里满是嫌恶:
【卖到窑子?你傻了不成?你仔细看看,这女的半边脸是烂的,没哪个妈妈(妓院老鸨)买,怕是倒贴银子都没人要。】
先前说话的马匪摸了摸下巴,眼中闪过一丝狠戾的淫邪:
【那依你说,怎生处置?我看把那半张脸遮住还能用其实。】
那马匪冷笑一声,抬脚踢了踢丁伶子的腰腹,见她毫无反应,胆子愈发大了,道:
【也行,就依你这般,先把她带回去,等咱哥俩玩腻了就把她拿去喂狼崽子。】
那马匪说干就干,一把将丁伶子的手腕扭到前面,缠了三圈,又狠狠打了个死结。他拽了拽绳索,见捆得结实,便将绳头往马背上一系,拍了拍马颈,咧嘴狞笑:
【走!】
那两个马匪没有把丁伶子挂在马上,而是选择像对待奴隶般的将丁伶子拖在满是碎石的地面上,两匹马扬蹄疾奔,绳索骤然绷紧,丁伶子的身体被拖着在碎石路上滑行,粗糙的石子如利刃般剐过她的皮肉,衣衫瞬间被划得粉碎,鲜血汩汩渗出,很快就在身后拖出一道蜿蜒的血痕,愈发的凄惨。
她的额头磕在石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可嘴里已经断断续续的念叨着素蛇。
两个马匪骑在马上,不时回头张望,看着她在地上翻滚挣扎的模样。实则不过是躯体被拖拽的本能晃动,发出阵阵粗俗的哄笑。
两匹马奔出约莫半里地,前头忽传出一阵清脆的环佩叮当响。
那两个马匪勒住缰绳,眯眼望去,只见月色之下,四个少女并肩而来,个个身姿窈窕,手里都抬着一根乌木轿杆,轿帘低垂,绣着暗金色的缠枝莲纹,瞧着竟有几分华贵。
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轿子?
两个马匪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瞧见了几分惊疑,随即又涌上几分歹意。
当先那个马匪啐了一口,翻身下马,抽出腰间鬼头刀,他指着那四个少女,厉声喝道:
【哪里来的贱婢?竟敢挡老子的去路!识相的赶紧滚开,不然爷爷一刀一个,把你们全都宰了喂狼!】
那四个少女闻声,齐齐停下脚步。她们动作整齐划一,将肩头轿杆轻轻往地上一放,乌木轿子落地无声,竟似有千斤之重。
随即四人转过身,对着轿子盈盈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动作虔诚得如同在朝拜神明。
马匪见状,扬刀又喝:
【装神弄鬼的,再不滚开,老子就把这轿子劈成碎片!】
话音刚落,轿帘微动,一只手缓缓伸了出来。
那是一只何等干枯的手,皮肤皱得如同老树皮,青筋暴起,指甲泛黄,指节处布满了老人斑,瞧着竟不似活人之躯,倒像是从棺木里刨出来的古物。
那手微微抬了抬,朝着最左侧的少女示意。
那少女得了命令,走到马匪面前,声音极其沙哑道:
【甲】“我家主人说:两位好汉,我的奴婢没长眼睛,放我过去吧。”
那两个马匪起初只觉这少女声音沙哑怪异,待她走近了些,月才那张脸竟毫无血色,白得像块刚从雪堆里刨出来的冻肉,眼窝深陷,瞳仁里没有半分神采,竟不是活人的眼神!
【飞僵!是飞僵!你们是弥勒邪教的怪物!】
江湖上谁不知道,目前天下唯一掌握飞僵技术的人乃是弥勒天国的欧阳居士,听闻他专爱滥杀无辜,以童男童女的精血来喂养飞僵。
后面其中一飞僵见吓着两个马匪,有些不好意思,态度温和的说道:
【乙】“两位误会了,有关爷爷的事情都是谣言,我们其实不吃那些………………”
那两个马匪已是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听什么辩解。当先那马匪怪叫一声,反手便将鬼头刀朝着说话的少女劈去。
可他们的兵刃离着少女尚有一尺之遥,却忽有个极快的影子击碎两位马匪的喉结,他们从马上摔下,一命呜呼。
那黑影落下,竟是其中一位少女,她看着地上马匪尸体,破口大骂道:
【丙】“操你娘老子,敢动手?”
【乙】“何必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就是因为你总是这样才坏了爷爷的名声。”
那位叫丙的飞僵性情颇为暴躁,不屑道:
【丙】“他们都快砍到你了,如果不是我,爷爷回去还要帮你把坏掉的部位缝好嘞!我看你才是最操爷爷心的那个。”
【甲】“够了。”
那两个正欲争吵的飞僵见甲已然开口,便退回轿子处不敢多言了,显然,在这四个飞僵之中,甲的地位远在其余三人之上。
甲缓步踱到马后,发现地面那道蜿蜒刺目的血痕,又落向被绳索拖曳着的丁伶子,随即指尖扣住丁伶子的手腕,轻轻一旋,便将那具失去意识的躯体翻了过来。
奇怪,这个女子身上没有伤口,那后面那因为拖拽而产生的血痕是怎么回事,还有,她的脸……………
就在这时,晕死过去的丁伶子忽然翕动了一下,气若游丝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含糊得像是梦呓。
甲俯下身,将耳朵凑得极近,也只捕捉到几个破碎的音节。
【乙】“这孩子说了什么?”
【甲】“听不真切,像是在唤什么……大哥。”
她转头望向那顶纹丝不动的乌木轿子,立刻躬身,请教道:
【甲】“主人,此地有个晕倒的女子,体质颇为奇异。”
轿内静了片刻,才传出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道:
【欧阳仇】“这样啊,荒山野岭的不安全,把她带上吧。”
过了几日,欧阳仇等人将丁伶子带到了东海的西廊岛上,但因为过度再生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她依旧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随着精力等逐渐恢复,丁伶子耳畔终于钻进些零心的讨论,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丙】“你们说,爷爷会不会把她也做成飞僵?”
【甲】“她和我们又不一样,我们是没办法救回来了才会被主人做成飞僵,她好端端的主人没事把她做成飞僵干甚?”
【乙】“她看上去也是个可怜的人啊,希望这孩子能长命百岁,醒来了看到自己这样不会太过伤心。”
【甲】“今天轮到谁给她洗脸了?”
【丁】“是……是我…………”
就在这时,一股温热的触感落在丁伶子的脸颊上,那触感接连移动着,从她紧绷的眉心,滑过鼻梁,又落在那半张溃烂扭曲的脸颊上,动作小心翼翼,竟没有半分嫌恶。
忽然,布巾停在了丁伶子的眼睫上。
丁伶子的眼皮,竟毫无征兆地轻轻颤了颤。
紧接着,她睁开眼睛。
丁瞧见那双骤然睁开的眼睛,只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布巾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就往门外冲,嘴里嘶喊着:
【丁】“醒了!她醒了!”
丁伶子只觉脑袋里一阵昏沉,目光扫过眼前几个少女的脸,那种毫无生机的肤色,不是书中记载的飞僵吗。
丁伶子害怕的死死攥着身下的被褥,蜷在床角,声音里带着害怕:
【丁伶子】“你们……你们是谁?”
见状,甲赶紧安慰道:
【甲】“姑娘莫怕,我们不是坏人,日前你在荒野昏迷,是我家主人救了你,带你来这西廊岛养伤。”
丁伶子的目光扫过周遭,这是一间简陋却干净的木屋,窗外传来海浪拍岸的声响,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咸腥味,竟没有半分血腥气。
就在这时,一道佝偻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欧阳仇,他脸上没有寻常老人的沧桑褶皱,反倒是透着一种玉石般的灰白,唯有一双眼睛,浑浊里藏着几分锐利。他走到床边,声音苍老却温和,听着竟有几分蔼然:
【欧阳仇】“姑娘醒了?身子可还有不适?”
丁伶子知道是这几人救了自己,就放下警惕之心,答谢道:
【丁伶子】“谢谢您,已经好多了,只是这里是哪里?”
【欧阳仇】“这里是东海的西廊岛,离我们捡到你的地方有些距离。老夫复姓欧阳,姑娘如何称呼?”
东海…西廊岛…这地方有些熟悉,等等,这里不是弥勒天国的领土吗,而且这个人性欧阳,莫非他就是臭名远扬的欧阳居士?不对,这人既然救了我,怎可这般想他。
【丁伶子】“小女姓丁,名伶子。”
欧阳仇闻言点了点头,道:
【欧阳仇】“丁姑娘既已无碍,若是记挂家中,不妨告知老夫你的故里所在,老夫遣人备船,送你返回便是。”
这话入耳,丁伶子只觉心口猛地一揪,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她才回答道:
【丁伶子】“不必了……我家里人……都死了。”
欧阳仇闻言,识趣的没有再多问,而是嘱咐道:
【欧阳仇】“既如此,姑娘便在这岛上安心养伤,待你觉得好些,我们再做打算。”
可旁边的丙却耐不住性子,上前一步,指着丁伶子的左脸,大大咧咧道:
【丙】“你家里人都没了,你这张脸,也是因为这事才变成这样的吗?”
【甲】“丙,你住口!”
【丁伶子】“脸?我的脸怎么了?”
她茫然地眨了眨眼,这才发现自己只有一只眼睛的视野,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手掌抚上自己的左脸。
指尖触到的,不是往日细腻光滑的肌肤,而是一片坑坑洼洼的触感,像是腐烂的树皮,又像是被虫蚁蛀空的朽木,凹凸不平的肌理里,还嵌着些微粗糙的颗粒。
丁伶子瞪大眼睛,不停的抚摸自己的左脸,像是在确认什么,撕心裂肺的喊到:
【丁伶子】“请给我一面镜子!”
甲被她这声凄厉的呼喊惊到,慌忙转身从墙角的木箱里翻出一面磨得发亮的铜镜。
丁伶子一把夺过铜镜,双手发抖,将镜面挪到自己眼前。
镜中,自己右半边脸尚且能看出昔日的轮廓,可左半边脸却早已不成模样。腐烂的皮肉皱缩着,露出暗紫色的肌理,几道狰狞的疙瘩嵌在肉里,左眼只剩下了眼窝。一半美,一半丑,一半人,一半鬼。
【丁伶子】“不…!”
她把头埋进铜镜里,开始哭泣起来。
【丁伶子】“天哪,天哪…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于一个曾经将容貌视为宝贝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现实是多么残酷。她只是正常的活着在这片土地上,却在短短一夜间经历了全家却平白无故的惨死。自己的清白,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容颜,自己爱慕的人,全都被轻易的碾碎,破灭,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
愁啊,她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剩下这满腔的委屈的仇恨,无处发泄!
丁伶子将手中铜镜掷在地上,铜镜碎裂的脆响里,她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嘶吼着便要往旁边的土墙撞去。
甲乙丙三个飞僵赶忙扑过去抱住她的腰,唯那丁胆小如鼠不敢上前,好个丁伶子,三个飞僵合力才堪堪将她拽住。
【甲】“姑娘莫要寻短见!容貌毁了可以再想办法,性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丁伶子的挣扎渐渐弱了下去,最后浑身脱力,瘫倒在三人怀里,哭的撕心裂肺,梨花带雨罢。
接下来的几日,丁伶子便如失了魂一般,终日枯坐在床沿,不言不语,也滴水不进。甲寻来的米粥温了又凉,凉了又温,始终不见她动过一口,每天唯一的动作就是捧着那破碎的铜镜看着自己的脸。
乙瞧着她这副模样,生怕她再寻短见,便趁她昏睡时,悄悄将那些碎镜片收了去,埋在院外的沙地里。
待到第七日的黄昏,残阳将海面染成一片刺目的猩红,海风卷着咸腥的潮气漫过木屋。甲正忧心忡忡地往灶膛添柴,一转头,竟看见丁伶子扶着门框站着。她身形单薄得像一张纸,她没说话,望着海边欧阳仇的背影,随后抬脚,一步一步,朝着海边断崖走去。
欧阳仇忽闻身后脚步声,就转过身来,便见丁伶子踩着黄草,一步一挪地行来。
【欧阳仇】“姑娘身子尚未痊愈,怎的跑到这风口浪尖来了?”
丁伶子不语,她在这七日里,尝尽了人间至苦,受尽了锥心之痛,昔日娇柔婉转的女儿家,如今只剩一身残破躯壳,满腔怨毒执念。
忽然,丁伶子断然朝欧阳仇跪下,道:
【丁伶子】“居士,我已经无处可去了,您就收我为徒罢!”
欧阳仇闻言,伸手似是想扶起丁伶子,指尖离她肩头尚有半尺,却又倏然缩回。
【欧阳仇】“姑娘快请起。老夫所修所学,皆是些损阴折德的旁门左道,学了只怕寿命不长。”
【欧阳仇】“我这岛上的四个奴仆,本就是当代医术救不回来的死人,老夫不过是捡了她们的残命,教些保命的邪术罢了。你尚有生路,何必与老夫这老朽,一同堕入这无间地狱?”
丁伶子不愿放弃,只道:
【丁伶子】“徒儿此生别无所求,仅凭我这身低微的武功,要待猴年马月才能杀到柢国报仇?只求师父收了我罢。”
欧阳仇见她如此,心里竟泛起几分罕见的波澜,那股决绝狠厉的劲头,竟与三十年前的自己如出一辙。
那时他也是这般,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跪在杨莲面前,只求一身能复仇的邪术,什么阴德报应,什么生死寿数,全抛在了脑后。
再说自己如今已是迟暮残躯,行将就木,一辈子的术法研究若就此带进棺材,倒也可惜。
【欧阳仇】“老夫活了这一辈子,杀人无数,造孽无数,本就没想着能善终。既然你这娃儿诚心恳求,那老夫便遂了你这个愿。”
那甲因心有担忧,就拎着锅铲过来,刚好撞见此幕,便道:
【甲】“好的很,这下咱也算是有个小主人了,走,咱带你去吃好吃的去。”
她将丁伶子扶起来,正欲带丁伶子吃饭,那欧阳仇却再次开口。
【欧阳仇】“不过…………”
【欧阳仇】“老夫既然收你,却不代表你以后是弥勒天国欧阳仇的弟子了。”
【欧阳仇】“你要谨记,你是武夷三十六派三仰派欧阳烈青的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