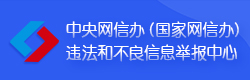畅游在世界里,鱼儿也会消散与诞生,抬抬头,是无尽的黑暗,和窒息的氧气。
原定的十二点的闹钟如一句元旦的祝福,尚未开始,但蓄势待发,我从清醒到现在,约莫半个小时才起来,已经是十一点五十四了。
“@全体成员 都还活着吗”
今天也要聚会,俗话说,没有元旦晚会,就自己创造元旦晚会,不过……已经是元旦期间了呢。那我换个说法,没有奇迹的话,就创造奇迹吧,这样,便开始下床准备了。
“@棍母 你明天来参加集会吗”
要说准备吧,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无非就是衣服、食物、杂物,不过有些人比我还快些,早在凌晨两点便开始问东问西。
“不然呢”
“@大肘子 他来嘛”
“不一定来”
比较可惜的是,总有些事如捉摸不透的风,脸上冷风过千番,在漱口时不得不清醒,清醒便要开始思考,也不由得感到心烦。琢磨一番,大衣刚才发货,校服不可御风,那不是没衣服了?可怜我至今没几件合身的衣服,在床上翻找几番,掏出件前年的外套便披上了,稍微有点短,不过还算合身。纯白的外套上有些污渍,帽子和四五个口袋是它最棒的特色,更别说还有棉内胆可拆装,不过我不需要就是了,毕竟这儿的冬天,还不算冷。
这时刷会儿视频是跳过时间的最好方式,也是不想去准备的最好方式,把今日的动态先发出去,高枕无忧,再收到袁子午的电话,匆匆下楼。
要说袁子午,快的名号莫非是他了,所谓疾如风,也是第一个过来的人,甚至在此之前还打上几把游戏怒发冲冠后才前来,实在令人佩服。
我们再上楼去,便唠起游戏的二三事,Kards被我卸了,便要他悲伤,瓦罗兰特没更新,便要他悲伤,不止是网络原因,不常玩网游便要他悲伤。于是看我点点头,把这俩下载了,究其这么喜爱的原因,大概是个环境问题,这也是这里被当成秘密基地的原因吧。
这么想,就要头疼起其余人的未到,只能继续准备了。拿起相机摆弄会儿,握手里有些担忧,挂脖子上又不觉舒适,好似有人在扯我脖子。没什么办法,只能调下绳子的长度,缩到最小也是贴在胃那儿,不过想想,无论是肚子还是胸口,好像这块区域是最抗打的了。
要说有什么是开心点的,低头看去,两个小挂件在我外套上舞着,是抬头的两个挂我床上的二次元公仔。因为没地方放,就挂我床尾了,和对边的捕梦网一起,算是祈祷能保佑些什么,也是装饰上的对称美。把他俩取下,是《葬送的芙莉莲》的塑料小人,一个菲伦一个修塔尔克,一个挂左口袋拉链的绳子上,一个挂右口袋拉链的绳子上,像是白色里多出些不小心的颜色,挺不错的。
而后又收到叶灵雨的来电,若不是我来回巡着,便发现不了手机静音的事,便想到本该有歌声的静音铃声连带着楼下那人的联络留言和那人伫立凛冽天气中,已是振聋发聩。
我下楼,问了除他俩以外其他人的事,一个不得不去参加饭局,一个了无音讯,便邀他上楼了。
哦,妈妈咪呀,怎会如此呢?若是不可为之事,作罢也无人啼嘘,可了无音讯就有些诡异了。便叫叶灵雨再打几通电话,继续准备去了。
外套可以藏相机,给拉链拉上,竟不觉得小了,也许是相机的大小给我拓宽了些,看不见里面的校服了。我见得拉链还有绳子,想再找一个小挂件,便想起去年抽到的假面骑士的橡胶钥匙扣,和我现在钥匙上那个是一个系列的,本想是高中时给它换了,现在提前点也不是不行。
可四处翻找,却不见影子了,越是寻找,越觉得奇怪,之前收起这些东西,现在怎么翻都是有记忆的东西,可那个假面骑士的钥匙扣是找不到了,令我翻箱倒柜地找,而那人不接电话,更是令我止步于这方寸土地。
我相信,叶灵雨可谓一灵字,便求助于他,可让他来寻找,也是无功而返。见那人还是没接通,时间可不会怜惜,三点出头,太阳是灰白色的,只能走了。
要说走去哪,这事早在元旦还没放假时就有了结果,叶灵雨在群里问道,我便回他KTV,他不接受,便又去爬山,只是不同于生日时去的莲花山,这次选了近的羊台山。也是就近原则,要去那刘辽文的家中设宴,顺便取回我的吉他。
不多时,便到山脚下,去整了烤肠来吃,自然是袁子午付钱,算是提前补充好体力。这卖烤肠的三轮上坐着一只土狗,通体土色,看着娇小,还一两岁,不过比刚出门见的那只瘸了腿的白狗要乖得多,至少不会乱叫,也肆意让人摸,只是我好像和它不是很熟,我要伸手去摸,突然就从爬着变站起了。
要上山去,就会想起去年九月十三的聚会,有道是出道即巅峰,我想聚会也如此,去水池不见龟,只有垃圾作祟,可我亲眼见得,那垃圾桶就在山上前的楼梯旁。
山上分两条路,一条往右去,是大路,用水泥铺成,缓慢而人多,但视野开阔,风景尚可。一条往左去,是小路,多为楼梯与少许似木的桥梁,这条更为多人,视野被树遮蔽,但革命名胜更多。
没多少思考,便往左走去,毕竟我曾言道:“登山路漫漫,小儿闲琵琶,分叉都向左,回来须往右。”
这往左走去,便是楼梯与曾经仙人打坐的地方,袁子午在这打拱,可惜没得仙人在。再上去,便觉得不对了。虽然我没找到那假面骑士的钥匙扣,还是在这拉链上挂了个秋山澪的亚克力板,然后再一看俩口袋,都是半拉上的,因为右边还揣着一瓶四百毫升的饮料,而内部除了已经挂脖子挂习惯的相机,还在内侧的左口袋里放了个相机镜头。通体的配重如死亡搁浅般精细,便是不带袋子和背包的后果,这BB还在撞我的腹部,不得不把手揣到口袋里一个护镜头一个护相机。
这太不对了,虽然有下山的小孩想看几眼挂件,我也觉得,咱为什么不向右去?可能这里的速度真的很快吧,沿途也听见袁子午在那说:“之前我到这里爬的时候,还能看到贼大一个蜘蛛。”
叶灵雨便回他“咋样啊蜘蛛?”
“好像是一只蓝色的蜘蛛在这两边。”
“哇这么稀有。”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说罢,向两边看去,“你看左边那还结了网呢。”然后便结束了。
山脚下,四周还是以水流和绿树为主的,路只有一条,所以往来都是些拄登山杖的人和玩水的人。先不说一个年轻人要登山杖干什么,便是老年人登上也可说无风险,更何况一个登山杖还要二十块钱。再是这水到了冬天,就如所有冬天的冷清,不剩什么,也尽是泥沙,有些源头水多些,才能看到点清澈的样儿,和数不尽的岸上的湖中的垃圾。
我想,要是共工所见,便要再次怒触了。几小儿在水上嬉戏,可不剩什么水,网里可捞不到鱼虾来,便去看岸上的父母,不知怎得就带他们下到看起来本下不去的地方了。如此想到:这垃圾也有重合性啊。
再往山上走去,大概是歌单的第三四首,山上没网,我也没提前下载,心里满是那假面骑士钥匙扣便出门,现今戴着耳机,歌单却是生日时听的那个了。这时便见到几片黄叶,在一众绿叶里显得突兀,好像现在是秋天一样,让我看到些芙兰朵露的影子,因为马上就到《おてんば恋娘》了。再登上去还有黄色的花,同样吸人眼球,可惜这花太小,可能春天会开花,可是冬天已来临,可再往上走了。到了处开阔的地方,有一铁栅栏把右边封上,说是未开放,就再往左去了。
远处能见大路的人,看着离山顶不远,路牌也是这么说的,可路牌说的是直线距离。再找处地方歇歇,后面有三俩孩童在玩水,这处亭子连接着大路与小路,前头还得上山去,看着些孩子的精力,不由得羡慕起来。
亭子有牌子,上面是革命英雄的事迹,这里蚊子多,蜻蜓也多,只是到了冬天,只剩下人和光秃秃的树了。其实树并不光,但这冬天的太阳太白,晃得我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去看。把我那饮料给众人分了几口,叶灵雨提议让袁子午给我们拍一张,便举起手机开拍,他坐最左,灵雨中间,我最右,拍出来便是灵雨最白,而我最黑了,算是了了当黑人的好奇。
再上山去,十分钟后,已是下午四点,望见远处又有一亭,感觉已是过了好久,如欧阳修偶见醉翁亭,又上前查看,是瞭望塔。
我愈发觉得炎热了,不是说这天,这天是冬的寒冷,没有外套便不行,可体力消耗绝对是热的,登上这台子,袁子午他们便熟悉起来。
“这段楼梯好像朝圣的那个登神长阶。”
“嗯,确实。”
他又问起我来:“你没感觉吗?”然后缓过神,“哦对,你没去过。”
大概说的是我生日那会儿的后续,不过我早早归家,也不到哪儿朝圣去了。要说这儿的风景,若能想个好点的词,只有“绿”了。满山的森林可谓孤寂,可满山的人就藏在其中,就如远处被雾缠住的城市,欲是觉得孤独,欲是想起这多人的孤独。
“别给你相机摔下去了。”袁子午提醒道。
“放心,要是相机能摔下去,我的脖子先被截成两半。”
下塔,更是热了,在栅栏上靠了会儿,累得不行,便觉得是那外套的错,给它东西塞吧塞吧就进叶灵雨的书包里,因为袁子午的袋子已经装了它的校服外套,我就只能把饮料放里面。一脱下,先不觉得身轻如燕,这冬日的冷风把我吹得发冷,与冒的冷汗形成联合,只能祈祷我的身体还算抗冻了。
“好冷啊……”
“你还觉得冷啊。”袁子午率先发问。
“bro有胃袋,我没有啊。”
“还真是。”叶灵雨一并附和道。
“你别给自己整失温了。”袁子午最后说到。我看着他在前面休息的亭子还穿着的外套不在身上,不禁笑了。
十分钟后,到一处革命遗址,便上前看去,原来是蕉窝村,左边还有处告示,写着些安全事项,袁子午看了看,苦笑着说:“看来我爸是不能登上来了。”拍下而离去。
再过两分钟,周围的绿色少了些,路也便宽了点,虽然楼梯还是这么窄,但道两旁不再被拦着,甚至看着可以走上去,于是作死的人也多了起来。这里有个描述此山的石头和些供人拍照的大石头,没怎么看就接着上山了。
又过六分钟,来了处狭窄小道,这里是毛泽东的题字,在远处便见得它的字体了。不过此处有两座大石头挤占着道路,拍下而离去,没有多看。
此处往后是寻常可见的超长楼梯,平视不见尽头,便再次休整,顺便检查下挂件,给我外套穿上。要说这路上是什么助了我,我想是音乐与友谊,是音乐与友谊的魔法。音乐的力量是使人振奋的,播到《老人与海》便步伐轻盈,播到《小小的海》便身轻如燕,恰如现在播到《ふわふわ时间》便冲上台阶,一骑绝尘。所以音乐的力量是功不可没的,遮蔽了人来人往的交谈声,专注起来了。而友谊便是那纯净的冬日般的白,唯有友谊是超越一切的爱,那不同于私人的爱,却是博爱了,那混成亲情般的友谊,便是友谊的力量了。
三分钟后,到了平缓的地带,有一亭子肮脏不堪,满地的垃圾与喝一半的水,塑料、纸、橘子皮、烟头散落四周,无从下坐,试图让自然来风化什么,只有清洁工整理着,如同这一路上随处可见的零食垃圾与想着就算扔了垃圾也有人管的垃圾。
再往前还有个亭子,这里就满是人了,与那边不可前去的污秽不同,这里有两层,和铁做的悬空楼梯,搁以前是不敢上去的,现在也是准备登高望远一番,后头一直能传来袁子午可能跌倒的叫声,前头架好拍摄点的叶灵雨正在拍摄我们二人。
登上前去,见得一老人挑担,担两头是蓝色塑料袋裹着的两大袋垃圾,背上是白色的双肩包,和他的黑色衣裤一样的纯粹。他见了这儿卖冰棒的老板,他和老板也笑嘻嘻地谈起来,便是应了那句话:“劳动者最欣赏的也是劳动者。”
再下楼去,他已走远,也许他不老,只是面容憔悴,头发稀少,看着,没别人年轻而已。
再过十五分钟,我把那些小挂件都收到裤子口袋里,因为太容易掉落,菲伦掉了两次,修塔尔克一次,不过秋山澪的铁扣子倒是屹立不倒了。
上层楼梯,没成想,竟走到了大道上,前方还是楼梯,楼梯前有个卖冰棍的人坐在那儿。
“这冰棍多少钱啊?”叶灵雨问道,老板说要五块钱两根,便踌躇起来。袁子午又问:“你们要不要吃?”我一口拒绝,而叶灵雨同意,老板也是三番五次地诉苦,便让子午拿定了要买。买来我也在他的邀请下尝了一口,好冻。便想到不久前说的“如果在冬天吃雪糕的话,就能让它化得慢一点,也就是说,能更多地品尝到它的味!”现在我看,这全是冰渣子的冰棍,也只能尝到水味,而不见红豆味儿。
吃了食物,见了大路,便不想回小路的疲惫,走大路去歇会儿了,反正都是向左嘛。
这里有站台一样的亭子,枯树,紫色的三角梅,更宽广的路与人,也许两边的人差不多,只是这里更广阔罢了,走来也尽是白色的日光与风,还有更少更隐蔽的垃圾。
也许柏油大路是有点不同,走段上铺,便见到一人站在石柱栏杆上,下面便是万丈深渊。北风呼啸,死盯着他,往来不绝者,莫过于风,即使有人走过也毫不在意,莫是不怕死,而把生命当儿戏,见他人过中年,还能说什么呢?寻刺激便如寻死,如赌博,不可估量,而人的渺小,在于看不见这山的全部,而毫不敬畏世界与生命。“你把生命当什么了?”
再上去,变得荒凉起来,就从树与树见看到了夕阳,冬季的夕阳,即是火红也见不得的白,仿佛冬天就是白,只有太阳本身是黄的,而太阳本身白得伤眼。
“啊……好久没见夕阳了。”我感叹道,“我感觉冬天不是白的就是黑的,现在终于见到点黄了。”让叶灵雨忍俊不禁起来。
朝夕阳的地方走到小路,再偶遇小野花,不同山脚的黄,它白色的花瓣在黄色的花蕊旁,标致极了,如同一朵儿童画的花,哪哪都这么符合印象而叫不出名。而途中多有些玩玩具越野车的人,占了两旁道路以外的土路,更显得这里的美好,除去那大部分的时间。
又过去七分钟,从原先的土黄与绿,山脚的绿开始多起来,也就是说,树多了起来,相应的,夕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沐浴夕阳的人。前方人员密集,叶灵雨一看便觉得是到山顶了,匆匆跑过去,而我们二人跑不快,就从另一处未施工的楼梯上去。
这里是小山顶,后面是扁平的亭子里的人们与前面栏杆前拍照的人们,空出中间的一点位子来。我探头去找叶灵雨,他在那儿拍照,观这儿的风景,我想是个人都会想拍一张的,主要是成就感。
袁子午在远处便见到:“那边的水是金色的!”
所谓水天一色,如此壮丽,城市风光,尽收眼里,可惜今天的大雾与多云和时不时欲下的小雨遮蔽了不少,就连夕阳也黯然失色。
下来,又要走一段长路,花上六分钟到真正的山顶。
山顶我看了,无非也就那样,与那亭子没什么不同,人是多了,挤在打卡点的,站石头上祝福打赏的,外放歌的,有垃圾桶的,和满地垃圾,比小山顶更多的垃圾。
我忽是觉得眩晕了,不是劳累,而是见得这景色竟不如小山顶,自然的人文的竟都是荒凉与荒诞,风好冷啊,没多看什么,便下山了。
下山不走原来的路,到别处去了。
别处也不见得好,见不得好的人在外放而不管他人,在随手扔垃圾即使垃圾桶就在不远处,在生死间游荡以显示自己的无畏与智商,在那对此不管的哑巴的眼里,沉默是默认了吗?还是有苦说不出呢?是懒得说了,还是看着看着,麻木了呢?为什么麻木了呢?是谁让他们有苦说不出呢。
十分钟后,见到一棵被裁剪的树,它似乎被裁成爱心,像是哪个情侣对树的讨伐,是树无声的呐喊,它们听不见,聋子自然是听不到哑巴与大多数说的话的。
往后也有不聋的人,三个人共用一台音响,争起要听什么歌。叶灵雨见了,便说道:“圈地自萌不好吗?”我附和,“用耳机不好吗?”毕竟我们三个都带有耳机,只是袁子午的耳机不是给他自己准备的,所以没戴着。
五点过半,天快黑了,几人虽是累得双腿疲软,也不得休息片刻,在上楼与下楼间乏力,望着似曾相识的难度三颗星,耗时三到五小时的土路,终于发现。
“我们走错路了吧?”
六点整,回到大山顶,子午在长途跋涉间竟比我消耗得更快些,大概是脂肪与一背包的东西发力了。大山顶人少了些,但人造的却多了些,灵雨同子午买了三根冰棒,一块钱一根,一起坐着吃起来,顺便把那瓶饮料一饮而尽。这儿的冰渣子少些,我终于能尝到除水以外的红豆味和绿豆味,以及包装上东莞的原产地。
袁子午是个速食者,与叶灵雨为了保护牙齿而用舌来舔不同,他用着这学期训练来的吃饭速度换得午休的些许时间,同时也必须不怕烫,不去想胃的事,只是,为了午休的睡眠时间。
至于我们为什么休息呢?是实在没力气了,爬上两小时半的楼梯,你爬你也麻。这时叶灵雨便提议拉伸一下,也许有用,为何不做呢?
此时已经歌单听完好久,开始翻起歌单外的,竟还有以外之喜,有些没被录入的歌就在内存里,就开始单曲循环些其他的歌来,如《響け!ユーフォニアム》这类更早的歌哼。这夜晚的风可谓极致,是极致的冷峻,鹓像发了疯似的,可该骂时,却指着又三郎笑起来了。
六点已至,便匆匆离开,叶灵雨一马当先,而袁子午前去买水,到了自动贩卖机,天已全黑。而这自动贩卖机似乎不识人形,没认出袁子午的脸来,也许是太黑了吧,虽没过多久,天也黑的太快。虽然但是,水还是通过扫码买到了,可喜可贺。
走大道,又过十分钟,到了我心心念念的风门坳,可不是太平天国的那个风门坳,这里在天黑下显得阴森,人也少了不少。
“你这拍得贼哈人,我要得不是这种感觉you know。”我对着袁子午的P图说道,“感觉它都不能庇我。”
而后他又去到左边的自动贩卖机那儿看看价格,百岁山,仅三块钱,也是他刚才买的那瓶。
别了风门坳,又过去十分钟,已六点四十,天黑得太快想走早就来不及。这山上在夜里可觉得不行,白日见不到的蛇虫鼠蚁可都来了,便贺道还好走得快,已经在大路上了。这时叶灵雨觉得实在太慢,三番五次加急向山下跑去,再到后面成了体系,便是袁子午体力不佳打前面做风向标,叶灵雨在后,而我再次居中,负责前后调动。
为了保护相机与镜头,我只能护着腹部跑,跑是跑不快的,但手也不用受更多的冷。一到晚上,前两个早在下山时就把外套穿上了,帽子定会被风吹掉,也只能让脸也受些冻,而感觉不到暖。
心里自是暖的,虽然黑暗如此,仍能在山上听到怪叫,看到手电筒,袁子午便朝那怪叫一起叫道。路上也能闲聊不少,从音乐到游戏到笑话,不知不觉,又是十分钟过去,找了两处地方休息,看不到头。
当然比起迷路登过两次山顶,还有什么更惊为天人的,便是袁子午的口哨,坐着休息会儿能听到他学的鸟叫,可谓一模一样,要是去花鸟市场,就是个德鲁伊了。
“南越有善口技者。”如此打趣道,“你再吹一段,我给你录个视频。”
录完,又再次合影,离开这里。如上述般跑步、休息、闲聊的变速跑,再唱上几曲,便听到耳机里的《ふわふわ時間》想着去年看番那会儿——“太他妈青春了。”
又到个转角处,我猛得想起,今天是元旦,最后一天元旦。
“话说其他几人怎么不来啊。”叶灵雨回:“刚才打电话也没接啊。”
“唉……”
微信步数也比其他人多得多,冲上了榜一的位置——一万七。只觉得大腿酸痛,脚底板发热,肺啊心脏啊劳累得很,再也不能跑,便一直走着了。虽是明白为什么初中的体力最强,换以前我根本不能走上四小时山路,还是不得不稍微放缓点脚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觉得该鼓舞士气,“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却只有袁子午跟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也算是预料之中,“要为~真理而斗争!”
询问原因,“我知道。”叶灵雨这么说,“这么做会有人把我们当嘉豪的。”
“那你理他干什么?”我回复道,“唱国际歌都能当嘉豪那你管他干什么?”
而后又过一段芦苇丛,我便想起跨年夜看的木鱼水心解说的《杀人回忆》,其中就有一幕,为芦苇丛袭击良家妇女,我便觉得那比人高的芦苇丛吓人。“等下从里面窜出来个野人给我吓死。”再到一环又一环的转弯,便见到一辆车从山上下来。“那天,偶见到一辆AE86,他辣过弯的芝士这偶辈紫都没借过。”望着月色,不禁让我唱起“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叶灵雨也有感:“月光华华~点灯来照菊花……”当然没少袁子午:“Vor der Kaserne vor,dem groen Tor,Stand eine Laterne,Und steht sie noch davor……”
“我想,还好我们三个还比较熟。”叶灵雨脱口而出,“你看我们三聊了四个小时,还能聊,要是换成不熟的,四个小时一句话不说闷死你。”
“还真是。”我想到,“其实这和表白是一样的,长途旅行和表白是一样的,要是不熟就不能邀请,就像表白也是,好感度没满表白了也是失败。”
“玩GalGame导致的。”令人啼笑皆非。
若是袁子午发话,我与叶灵雨便是异口同声,同步率400%,若是我们其中一人发话,便不会落下,毕竟这夜静的吓人,只有《天使にふれたよ!》民间粤语版的歌声和我们的闲聊声。
似乎,这路途没有尽头,都是名为青春的镜头,你一句,我一句,便说这时间匆匆,匆匆夺去了这经历。我便匆匆看到了城市的样子,“夜之城”是我给它最好的名字,冷血的充满差距的夜之城,纸醉金迷与砥砺前行的夜之城,如同十多年前的夜上海,也和今天的上海没什么不同。
“夜深圳,夜深圳,你是个不夜城。”我用蹩脚的粤语唱起这段话,“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袁子午依旧用普通话接着唱起开头。
七点三十六,下山了。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样呦,别的那样呦,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望着风刮起的跳舞的叶子,叶灵雨脱口而出“看,叶子在跳舞。”这是我们所不能比拟的文学思维,要让我来说,只会是叶子在风中起舞。广场舞是没有的,就把水分完吧,当做下山的奖励。
“开始是我们三个人,结束也是我们三个人啊……”袁子午感叹道。
“是我们三个吗?”我疑惑着,“对啊……”叶灵雨便从建群之初开始说起。
“的确是我们三个啊……”三个一年不到的友谊。
下山后无法去那未接通的家,无法摸到吉他,便到我家去吃。去吃汤圆、泡面捞面、自热米饭,听着我找来的一个小时的歌单,背着我早已选好的壁纸,在这方寸大小看着方寸的五人合照吃饭,“牢刘啊,牢刘!”抱着他的照片哭丧,“我找到原文稿啦。”在房间打转,然后差不多时便去赏月。
赏月,月的圆早在下山路就已看厌,只是若不去赏,就是离开了。我下楼去,虽然体验了百八十回上楼梯的苦,去找个地赏月,可没地是开阔的,没地是城市所能容纳的,便让叶灵雨离去了。
袁子午再去我家打打游戏,也一同离去。
离别不该是伤悲的,毕竟以后还能见面,即使是最后的元旦,也该断然他们的离开,毕竟人最怕的孤单,也是在渺小与无人在意中形成的。
“听见吗,旋律娓娓,迎新变化,并非结尾,往昔与未来,是会串连一起,直到永远,心始终有彼此印记——”
若是鱼儿不可抬头,也能低头去看看,身后的深海,与新生的迷途之子。
ps:有道是出道即巅峰,我看这《最后的晚餐》真的是我翻不过去的一座大山了,无论后来我的文笔再怎么精美,也看不到似那天的美好了。还有就是,我的腿好疼啊QWQ
借物表:
《相遇天使》粤语版 BV1pm4y1a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