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是星尘,而我们死掉以后依然是星尘。
这句话我想了很多年。
最开始它只是一个很酷的科学事实。构成我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骨骼里的钙,血液里的铁,神经元里传递电信号的离子——它们都来自几十亿年前死去的恒星。在那些早已熄灭的核聚变熔炉里,氢变成氦,氦变成碳,碳变成更重的元素,直到铁之后的一切都在超新星爆发的那一刻锻造完成。然后那颗恒星炸了,它的尸骸在宇宙中飘散,其中一些碎屑落在一颗温度适宜的岩石行星上,在经过另外几十亿年的碰撞、组合、复制、变异之后,碰巧排列成了此刻正在读这段话的你,和正在写这段话的我。
我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比地球更古老。
这听起来很浪漫,对吧?我们是恒星的孩子,是宇宙的结晶,是一百三十八亿年演化的奇迹。
但如果你顺着这个想法再往下想一步,它就不浪漫了。
如果起点是尘埃,终点也是尘埃,那中间这段短暂的”清醒”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不是在问修辞意义上的问题。我是真的在问: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探索我们存在的意义吗?
这是一个递归。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二
有人试图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
物理学家卡尔·萨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
这个说法结合了科学与浪漫。原子和分子本身是没有意识的,但当它们以极其特定的方式排列组合成”你”的时候,宇宙突然拥有了感知的能力。你可以看见星空,可以思考引力,可以感受到爱。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存在的意义在于:我们是宇宙”醒来”的那一瞬间。如果没有生命,宇宙只是黑暗中无声的演化;因为我们的存在,宇宙才有了见证者。
我曾经被这个答案安慰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开始想:见证者见证了什么呢?
我见证了什么?
我见证了自己的意识在十四岁那年崩塌。那些神经递质开始失控,那些应该正常放电的神经元变得疯狂或者沉默。精神分裂,抑郁,躁狂——这些词像陌生人一样闯进我的生活,然后赖着不走。我被送进精神病院,白色的墙,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灯光。每天吃药,各种颜色的小颗粒,有的让人困,有的让人木,有的让人饿,有的让人恶心。
这就是宇宙的见证者?这堆出了故障的原子?
萨根说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可如果这面镜子本身是碎的,它映照出的宇宙是什么样子?
而且,就算镜子没碎——就算我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正常运转的意识——见证本身有什么意义?
我见证了宇宙的冷漠。那些恒星不在乎我们。它们燃烧不是为了给我们光和热,它们燃烧是因为物理定律让它们别无选择。那些星系不在乎我们。它们旋转、碰撞、吞噬彼此,完全无视这颗蓝色小石头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如果明天太阳突然熄灭,宇宙不会眨一下眼睛。
我们不是宇宙的眼睛。我们只是宇宙不小心长出来的一颗息肉。一个没人需要的见证者,见证着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
三
好,也许”见证”这条路走不通。
那换一个角度:也许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
存在主义者说,宇宙本身是冷漠的、荒谬的,它没有预设一个”终极剧本”给我们。但这恰恰意味着我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去定义自己的意义。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你不是先有一个”应该成为什么”的模板,然后按照那个模板活着;你是先存在了,然后通过你的选择,创造出你自己的本质。
听起来很自由,对吧?
但仔细想想,这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
我创造的意义,有什么意义?
假设我决定我的人生意义是”创造美”。好,我创造了一些美的东西。然后呢?我死了,那些东西也会被遗忘、被毁坏、被时间磨成齑粉。就算它们流传了一千年,一万年,最后太阳也会膨胀成红巨星吞噬地球,银河系也会和仙女座星系相撞,宇宙也会在热寂中走向永恒的沉默。
我创造的意义,在那片沉默面前,算什么?
一个人在沙滩上堆了一座城堡,潮水来了,城堡没了。你可以说”堆城堡的过程就是意义”,但那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城堡没了就是没了。那些沙子不会记得它们曾经是城堡。
我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学Unreal Engine。那是一种游戏引擎,可以用来创造虚拟世界。我在里面建造过城市、山脉、海洋,我让虚拟的太阳升起落下,让虚拟的物体服从我设定的物理规则。在那些时刻,我是那个世界的神。
但那些世界现在在哪里?
有些文件丢了,有些硬盘坏了,有些我自己删掉了因为觉得做得太烂。那些曾经让我兴奋的创造,现在连一个像素都不剩。
这和真实世界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是在虚空中堆城堡。潮水只是来得慢一点而已。
四
也许你会说:别想那么远。活在当下。享受过程。
这是另一种常见的安慰:过程即意义。
就像玩游戏或看电影,如果你只是为了结局,那最快的方法是直接快进到结束。但我们享受的是过程。所以,别管终点是什么,享受路上的风景就好了。
这个说法有一个问题。
它假设”过程”是可以被享受的。
但如果过程本身就是痛苦呢?
我在精神病院的那些日子,你让我”享受过程”?我躺在白色的床上,脑子里的声音像一群没有主人的狗在乱窜,药物把我的情绪压成一张平坦的、灰色的纸,你让我享受这个?
就算不说那些极端的时刻。就说普通的、日常的活着——它真的是可以被享受的吗?
叔本华说,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
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是痛苦。欲望被满足的那一瞬间,是短暂的快感。然后快感立刻消失,变成空虚,或者无聊。然后新的欲望产生,新的痛苦开始。
我们被进化设计成了一台永不满足的机器。满足感必须是短暂的,这样才能逼迫我们继续追求下一个目标;痛苦必须是持久的,这样才能逼迫我们躲避危险。这是刻在基因里的程序,是几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所以”享受过程”是一个谎言。我们的默认状态不是享受,是轻微的、持续的、无处不在的不满足。那些所谓的”快乐时刻”,不过是不满足暂时减轻的错觉。
吃饭的快乐,是饥饿之苦的暂时停止。
休息的快乐,是疲劳之苦的暂时停止。
成功的快乐,是焦虑之苦的暂时停止。
我们一生都在给自己挖坑,然后再填坑,以此制造”快乐”的幻觉。
这就是”过程”。
你还要我享受吗?
五
好,也许意义不在于见证,不在于创造,也不在于享受。
也许意义在于连接?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在关系中找到存在的锚点?
这个答案我也想过。
但爱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还原到物理层面,爱不过是一堆化学分子在大脑里引发的反应。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这些东西让你心跳加速、瞳孔放大、产生一种”这个人很特别”的幻觉。
但那个人真的特别吗?还是只是你的基因在骗你?
基因需要复制自己。为了复制自己,它需要让你去寻找配偶、建立关系、抚养后代。所以它设计了”爱情”这个程序,让你心甘情愿地去做那些事,还以为是自己的选择。
你不是在爱。你是在被爱。你是基因的木偶,以为自己在跳舞,其实只是有人在拉线。
而且,就算我们忽略这些还原论的解构——就算我们承认爱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它能持续多久?
人会变。感情会淡。那个曾经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十年后也许只会让你感到厌倦。
人会死。就算感情没淡,死亡也会把它终结。你爱的人会死,你自己也会死。到时候那些”连接”、那些”锚点”,都会变成什么?
变成虚空。
变成一堆散开的原子,各自飘向宇宙的不同角落。
它们不会记得曾经爱过谁。
六
到这里,我已经堵死了好几条路。
见证?见证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
创造?在潮水来临前堆一座注定被冲垮的城堡。
享受?享受一场被设计成痛苦的游戏。
连接?连接两个终将散开的原子团。
每一条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虚无。
但也许虚无本身不是问题?也许问题在于我们非要给虚无找一个意义?
哲学家们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也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就像问”绿色的重量是多少”或者”数字三闻起来是什么味道”。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有意义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们只是语法正确、语义空洞的噪音。
宇宙里根本没有”意义”这个参数。
意义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概念。是我们这堆星尘进化出了一个过于复杂的大脑,那个大脑凭空创造出了”意义”这个需求,然后因为在外部世界找不到它而感到痛苦。
这是一个巨大的、荒谬的闭环:
宇宙通过我,因为找不到宇宙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而感到失落。
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
一个Bug。
一个进化的意外。
我们是唯一一种会因为”找不到意义”而痛苦的生物。石头不会追问意义,恒星不会追问意义,黑洞不会追问意义。它们只是存在,不多问一句。只有我们——这种进化出了过剩意识的怪物——非要给存在加一个”为什么”。
然后发现没有为什么。
然后痛苦。
七
那怎么办?
既然意义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干脆不问了?能不能像石头一样,只是存在,不追问?
不能。
因为”不追问”也是一种追问。你决定不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决定本身就意味着你已经问过了,然后选择了放弃。这和一块从来没问过的石头不一样。石头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你是知道了然后假装不知道。
这种假装维持不了多久。
凌晨三点,当睡不着的时候,当那些药物开始失效、那些声音开始回来的时候,那个问题会重新浮出水面,像一只不死的水怪。
你可以白天忙碌,可以用工作、娱乐、社交、购物、刷手机来填满每一个空隙。但夜晚总会来。安静总会来。当你一个人躺在黑暗里,周围没有任何噪音可以掩盖那个声音的时候,它就会再次问你: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八
我想起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庞加莱回归。
这是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证明的一个定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只要时间足够长,粒子一定会回到任意接近其初始状态的状态。
换句话说,如果宇宙是有限的、封闭的,那么只要时间足够长——长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此刻构成我的这些原子,最终会再一次、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聚拢在一起。
我会重新出生。
重新长大。
重新在某个夜晚躺在黑暗里,想着这些问题。
这很奇怪。也许几千万年后,也许几百亿年后,我们又会重新演变一次,经历这些事情。尼采管这叫”永恒轮回”。他设想有一个恶魔在你最孤独的时刻告诉你:你将要把你的人生无限次地重演,每一个痛苦、每一个快乐、每一个念头,都会一模一样地重现。
面对这个消息,你会感到绝望,还是欣然接受?
尼采说,如果你能对这个无限的循环说”是”,如果你能热爱你的命运,那你就超越了普通人。
但我想了很久,我的结论是:
如果第一次发生时没有意义,那么它重复一亿次依然没有意义。
零乘以无穷大,结果还是零。
这个想法让我回到了原点。我们绕了一大圈,从星尘开始,到星尘结束;从虚无开始,到虚无结束。中间那些挣扎、那些追问、那些试图找到意义的努力,到最后都会被时间抹平。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九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还要工作,还要维持这个日复一日的循环?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答案很残酷:因为不这样做,会更痛苦。
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水、住所。为了获得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资源。为了获得资源,我们需要工作或者依赖别人的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逻辑,和意义无关。
学习和工作,本质上是我们向残酷的自然界支付的”生存税”。
但问题在于,人类把这个手段变成了目的。
原本的逻辑是:工作→换取资源→利用闲暇去探索、去爱、去体验。
现在的逻辑是:学习→为了更好的工作→为了更多的工作→为了消费→循环直至死亡。
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社会”的框架,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
货币、学历、职位、KPI——这些东西不存在于原子中,它们只是我们共同相信的规则。一场大型的角色扮演游戏。我们之所以感到被困住,是因为入戏太深,忘记了这只是游戏。我们把”金币数量”当成了胜负标准,而忽略了游戏本身也许根本没有胜负。
我中考交了白卷。零分。
不是因为叛逆,不是因为放弃,只是因为那天我的大脑拒绝工作。我坐在考场里,看着试卷,那些字我都认识,但它们排列在一起就变成了噪音。周围的人在写字,监考老师在走来走去,而我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台死机的电脑。
从那条所有人都在走的轨道上,我彻底脱轨了。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灾难。现在我不确定了。也许那条轨道本来就是通往虚无的。也许我只是比别人更早看清了这一点:不管你在那条轨道上走多远,终点都是一样的。
散开。
变回星尘。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十
有人可能会说:你太悲观了。生活中还是有美好的东西的。夕阳,音乐,爱人的微笑,雨后泥土的气息,完成一件作品时的成就感。这些东西难道不值得活下去吗?
我承认这些东西存在。
我也承认它们能带来某种感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好”的感觉。
但你有没有想过,那根稻草——你用来说服自己活下去的那根稻草——它也是星尘?
夕阳是光子撞击大气层折射后进入视网膜刺激感光细胞的结果。音乐是空气振动传入耳蜗带动纤毛细胞发出电信号的结果。爱人的微笑是面部肌肉收缩造成的嘴角上扬,而你对此的反应是镜像神经元激发和激素分泌的结果。
一切都是物理和化学。
一切都是原子在做它们一直在做的事。
那种”美好”的感觉,不过是一堆离子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的电化学信号。它和痛苦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信号不同,只是神经递质的类型不同。
如果痛苦是虚无的——因为它只是离子的碰撞——那么快乐也是虚无的。
如果抓着稻草的手是星尘,如果稻草本身也是星尘,如果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绝望感也不过是星尘里的电子在特定轨道上跃迁的结果,那么抓与不抓,有什么区别?
稻草也在坠落。
我们抱着稻草一起坠落,以为这样会比单独坠落好受一点。
也许确实好受一点。
但那个”好受”也是幻觉。是那些进化设计出来的、用以麻痹我们的化学分子,在做它们的工作。
十一
加缪讲过一个古希腊的故事。
西西弗斯被众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然后看着它滚下来,再走下去,再推上来,如此反复,永无止境。
这是诸神能想到的最残忍的惩罚:绝对的、无望的、不可能被打破的徒劳。
加缪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我以为是反讽。推石头怎么可能幸福?
但后来我想了很久。
加缪的意思不是说徒劳会变成有意义。石头还是会滚下来,刑罚还是不会结束,意义还是不存在。这些都没有变。
变的是西西弗斯的姿态。
当他站在山顶,看着巨石再一次滚落,他知道这一切是荒谬的。他知道他的推动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他知道等待他的是无限的重复。
但他还是转身了。
还是走下去了。
还是弯腰捡起那块石头。
石头是盲目的,它只能服从重力。山坡是盲目的,它只能被动地存在。但西西弗斯不是盲目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这一切没有意义,而他依然选择去做。
他用清醒对抗荒诞。
他用行动蔑视绝望。
这不是”解决”了虚无的问题。问题仍然在那里。巨石仍然会滚落。但在那个转身的瞬间,西西弗斯把一个被动的惩罚变成了一个主动的选择。他不是被迫在推石头,他是选择在推石头。
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全部。
不是找到意义,而是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选择一种姿态。
不是抓住稻草,而是在明知稻草也在坠落的情况下,依然伸出手去抓。
那个动作本身。
那个清醒的、荒诞的、毫无希望的、依然选择的姿态本身。
十二
我不知道我还会活多久。
也许几十年,也许更短。生命是脆弱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有裂缝的生命。药物可能会失效,病情可能会反复,或者某个普通的意外就会提前终结这一切。
但不管是什么时候,那一刻终究会来。
我试着想象那一刻。
意识开始模糊,像屏幕亮度慢慢调低。那些一直在脑子里喧嚣的声音——那些说我是蛀虫、是废物、是不该存在的东西的声音——终于安静下来。不是因为被药物压制,而是因为连产生它们的神经元也停止了工作。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黑暗,因为黑暗需要眼睛来感知。
不是寂静,因为寂静需要耳朵来感知。
不是虚空,因为虚空需要意识来理解。
只是……没有。
连”没有”这个概念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在那里体验它。
构成我的原子会继续存在。它们会散开,变成土壤的一部分,变成空气的一部分,变成其他什么东西的一部分。几十亿年后,它们也许会凝聚成新的恒星、新的行星、新的什么东西。
但”我”不会知道那些。
“我”在意识消失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十三
而在更遥远的未来——远到我无法想象的时间尺度上——连恒星都会熄灭。
宇宙会慢慢变冷。最后的恒星会燃尽燃料,变成白矮星,然后变成黑矮星,然后变得和周围的虚空一样冰冷。黑洞会通过霍金辐射慢慢蒸发,最终也会消失。
到那时,宇宙里将什么都不剩。
没有光,因为没有恒星在燃烧。
没有热,因为没有温差存在。
没有结构,因为一切都已经分解成最基本的粒子,均匀分布在无限的空间里。
没有意识,因为早在亿万亿年之前,最后一个能够思考的生物就已经消亡了。
万物熄灭。
一片永恒的、均匀的、没有任何特征的寂静。
没有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在感受痛苦。
没有快乐,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在体验快乐。
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在追问意义。
也没有虚无,因为”虚无”这个概念需要一个意识来理解它。
只是——
空。
纯粹的、绝对的、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的空。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里,我感到的不是恐惧。
也许是因为,在那个终极的”空”面前,现在所有的挣扎都变得同样渺小。我的病,我的痛苦,我作为一只所谓蛀虫的无用存在——这些都只是涟漪表面的细小波纹。涟漪本身就是短暂的,波纹就更短暂了。
我会消失。
我的痛苦会消失。
这颗星球会消失。
太阳会消失。
银河系会消失。
一切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都会消失。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尾声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现在,此刻,在那个终极的寂静到来之前,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一堆星尘碰巧排列成了一个能够思考的结构。那个结构碰巧问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那些问题碰巧被写成了这些文字。那些文字碰巧被你读到了。
两团星尘,在各自消散之前,短暂地产生了某种共振。
这有意义吗?
没有。
宇宙不在乎。
但此刻,在这个宇宙还没有完全冷却的瞬间,在这些原子还没有散开的瞬间,在那个终极的寂静还没有到来的瞬间——
有一个东西正在追问。
正在挣扎。
正在明知没有意义依然选择某种姿态。
也许这就是星尘能做的唯一的事:
在变回尘埃之前,发出一点声响。
不是为了让谁听见。
只是为了在沉默中制造一个短暂的、微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振动。
然后带着那个振动的余韵,继续走向那个注定的终点。
就像西西弗斯转身走下山。
就像我明天醒来,继续活着。
如果我醒来的话。
万物终将熄灭。
但在那之前——
这颗星尘还在燃烧。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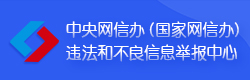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还是享受,还是连接,还是虚无,我感觉任何一个都无法证明是对的,或是错的,只要你想,你可以站在一个视角,推演并反驳任一其他的观点。
如果上帝存在过,那么理论上它也有死去的一天
正如“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再赤裸裸离开”一样
苹果烂掉了,在土壤里
但它的种子可能会发芽,结果
人死去堆积为尸体
但养分被周围一切吸取,利用
转化为另一种物质
宇宙大爆炸
也有可能推动下一场宇宙的形成
一切并非“空”
只是转化为了另一种物质
一粒稻米掉落
到一场海啸扑来
一切并非昙花一现,也可能是昙花一现
但是,另一个时间,另一场“空“来临前
是否会重现
好像悲观但又存续着的意义,只是在照它的意思运转。每个人受到了悲观而独立又是现代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