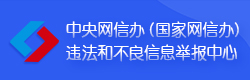临近暑假,学长学姐们要毕业了,所以这几天总能看到他们在路边的跳蚤市场,卖一些零碎玩意。刚好,我对这充满市井味道的场面挺感兴趣,就沿着路边一个一个摊子地看过去。摊子上没什么特别的东西,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但有一个摊位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表情麻木的学长,深深的头发半掩了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路边;面前的一大张纸上,摆着他唯一要卖的商品:一个U盘,不仔细看,你甚至看不到这个他要卖的东西。我顿时来了兴趣,上前一问,这U盘16G,五块钱,还能用,里面是他写过的一些文章。我于是带着莫大的好奇买了下来。学长收了款,收起纸张,幽幽地离开了。并没有留给我追问的机会。
我回到宿舍,插上U盘一看,没有损坏或扩容,是个正品;学长所说的文章也有,但不多,基本上都是些伤春悲秋,青春感怀之类的无聊文章,我随便看了几篇,都粗劣得很。其中只有两篇文章还算有趣,但也说不上优秀,我便放出来,姑且供大家解解乏:
篇一《过不去的桥》
我和我爸打算去隔壁山头爬山。我骑着自行车,他开汽车。因为我们这里处处是山,公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我叫他开车不要开太快,让我刚好能骑车追在他后面——你问我为何不坐车?我就是不想闷在车里被动地弯来绕去呗!自己骑车呼吸新鲜空气多舒服。
今天天气挺好,满天的云朵盖住了耀眼的太阳,不会让我感觉很热。我在公路的内侧骑车,和我爸的汽车保持着不近也不远的距离,我朝前方看,刚好能看到后视镜里我爸的脸。这里虽说是山区,但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竟也不少。因为我们前进得慢,基本上都在被超车。每次有车辆经过,我都紧紧地眯着眼,生怕扬起的沙尘迷了眼睛。
今天要去的山,我爸小时候去过,和我们这里的山隔着一个有溪流的山谷,听他说,那时候溪水还很浅,脱了鞋,卷起裤腿就能淌过去;后来溪水多了起来,便渐渐地湍急了,四周有几座城镇,经济一发展,桥上便架起了立交桥——这些都是他听别人说的,他自己也有十多年没去过了,也不知道这桥是什么样子——更别说我了。
不多时,我们便到了这山谷。我爸把车靠边停着,摇下车窗,感叹了几句时过境迁之类的话。而我只看到一座灰扑扑的立交桥,上面的车流绵绵不绝,在两座山之间穿梭不断。但我不好描述这座桥的具体结构,它由两三条来自不同方向的公路穿插而成,看不清里面具体的走向。正看时,我的背后开来一辆鲜红色的小轿车,飞快地开进立交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已经出现在对面山上的一个广告牌下面了。
“还不走吗?”我对着我爸那边喊话。没有回应。
我走过去,看到我爸一脸困惑地拿着手机:导航系统上没有图像,显示这无信息的字样。
“没信号啦?流量也不行?”我拿起我的手机,打开导航软件,一样的界面。
“刚刚我看还有信号的,怎么到这里就没了?”车里传出我爸疑惑且不耐烦的声音。
“算了算了,自己开过去呗,这一座桥而已,转几下就过去了。”
“也行。”我爸发动了引擎。
行至桥前,路分岔成了一上一下两条,我跟着我爸往上走,然后突然一个下坡,光线变暗,我立刻捏紧了刹车,险些失去平衡:我们现在似乎是在另一条路的下面,沿着弯曲的道路前进,光照突然又变亮,我们驶出了大桥。
“你看,这不就过来了吗?”我一脸自信地环顾四周,却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广告牌。我心头突然一紧,更加仔细地看了四处,发现那广告牌是在对面,我们爷俩还是在来时的一边,仅仅是比原来的位置前进了一点。
他也很困惑:“嘿,怪事?走错了?”
此刻,我还不慌,走错就走错了呗。“换一条路不就是了?”我跨上单车,往回骑上了桥,这次是走下路。嗯,不会错的。
于是我和我爸返程,继续上桥。骑上桥的下路,我的视线就暗了,但好在路线没有弯曲,直直地过去了;大概也就十几秒,我们就下了桥。这下总没错吧?
我回头一看,身子顿时僵住,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还是那个广告牌,还是在对面,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在一开始的位置稍稍往前。
怎么可能?明明只有两条路?为什么这么都过不去,这不是纯纯浪费资源修了条多余的东西吗?
但我的疑虑又被瞬间打消,因为路上确实有来来往往的车辆,山谷的这边、那边和桥上都是。仔细看,的确是这边的车上了桥,随后出现在有广告牌的那边。我仔细地记着那些车的数量和颜色:数量上都对的上。
此时看我爸那边,他已经是肉眼可见的焦躁了。我让他停在原地别动,我骑车去桥上看看。
骑上车,我沿着桥的上路前进,一边避让着身边擦肩而过的车辆——他们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一边仔细地看着道路边缘。我慢慢地骑车,突然眼前一亮,原来在路上这里还有一条小道,刚好能让一辆车开进去!我于是喜滋滋地上了这条路,这是条长长的下坡;骑着骑着,我就到了溪流边,然后我立刻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这条路是沿着溪流延伸的亲水道路,根本就过不了河。我懊恼地刹住了车,把车头调转。看向那条溪流:
听我爸说,这河以前是可以一个人淌过去的,不过现在,我看不行,这河大约有二十米宽,河里乱石和激流一个接一个,贸然下水可是会被直接冲走的。
我郁闷地往回骑,脚下一用力,才回过神来:我下来时是一个很长的下坡,这回我得踩一个很长的上坡了。本来我再此前已经蹬了很久的车了,又在这怪桥上上上下下地来回,又遇上这么一个长上坡,等我终于到了水平路面上时,我已经没力气踩下去了。我选择下车推着走,大腿上的肌肉紧绷得厉害,如果此时有人好奇地来看我的话,他一定能看出我的走姿非常的不协调。但我还是不死心,这桥这么就过不去呢?我继续推着车,换了另外一条上坡路,依旧是观察着路边,看是不是有什么漏掉的缺口。
我把车停下,看着路边这条小路,心里满是纠结。因为这条路不是给机动车走的,完完全全就是条宽点的土路。我站在路口思考片刻,还是决定下去看看。这条路十分颠簸,而且两边都是杂草和茂密的枝丫。大概前进了二十多秒,当看向前方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条路甚至是条死路,尽头被桥墩截断,并且隐约可以看到前方的河水。
事已至此,只好回去了。我艰难地把车往上推,回来时的路口去。此时正好一辆越野车上了桥,我看着它开进立交桥里,在短暂地被挡住视线后,出现在山谷对岸那块广告牌下。
爸爸的车就停在路口等我。他看一眼我的神情,就知道我是无功而返了。我问他这边的情况,他说,他拦下了几辆车问路,不过这些人有的是不上桥,有的是直接从桥对面过来但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也向几个人解释了我们遇到的麻烦,但那些人都表现得像见了鬼一样,不敢再搭理他。
我们就这样在路边,看着对岸,什么话也不说;过了一小会儿,我说要不我们回去吧。爸没有接话,只是转身钻进了车里。我骑上了自己的车。
回到家里,我们只说这半天在公路上逛悠,我妈还挺可惜地说没去哪个具体点的地方玩。再之后,我们谁都没有提过再去那座桥。
生活还在继续。后来,我生日那天,我爸爸的一位朋友,从山谷对面那座山上的亲戚家里拿了点腊味送给我爸,还送了我一个精致的蜻蜓标本。再后来,村里徐伯的大儿子娶媳妇,那个年轻姐姐的娘家人就是那座山上的。几年过去了,依旧时不时的有来自那座山上的消息,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再去看一下?
但我终究没有再去;它似乎只成了我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印象。
篇二《卡在树上的弹力球》
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用力地眨眨眼——嗯哼,倦怠。我为什么倦怠?还不是这个无聊的运动会!今年这天气格外的热,按理来说是个开运动会的好时间,可是谁能想到这么热!即便不动,光是站在这太阳下,皮肤就被光线灼烧得发烫了。偏偏学校还不允许我们躲在教室里避暑——即便是观众也要有观众的责任?算了,我摇摇头,快步地从树影下走过。
我手里拿着一个弹力球,这是我曾经的好朋友送我的分别礼物,那会儿我们还小,买不起多么贵重的东西。一个弹力球,在小学生里都是至宝级的玩具了,更何况这是他送我的礼物!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将它带在身边,闲来无事就弹几下,看着它高高地蹦起,再一把接住——
当然,总会有没接住的时刻。一个不小心,这球可就蹦蹦跳跳地跑老远了——最害怕的是蹦到下水道里去,幸好这档事还没有发生过。这几年来,最不济的情况是弄丢过几回,当时可真是急到我了!还好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最多不过半天,它就在某个角落里被我掏出来了。
我现在躲在道行树下的阴影里,虽然不会被火辣辣地直晒,但这高温空气中沉闷的水汽还是让人难受。听说四楼一个班上有个女生中暑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很鄙夷地哼了一声,就当是我对这运动会的诅咒了。烦躁,这么热的天还不让人待教室里。这会子又有人热出问题了,虽说不会有大事......
“烦人诶!”我用力地嘀咕了一声,把弹力球往地上重重一砸——我习惯性的抬头看,空中移动着一个五彩斑斓的点,那点先变小,然后停住,然后慢慢变大,我伸着手准备去接:
“卡住了?”我吃惊地叫出声来。
的确,似乎是被风吹偏了一点,这球不偏不倚地卡在了树的枝桠间,离地面足足有接近两层楼米高。我不禁抱怨自己当时不该砸那么重。这怎么拿下来呢?
我先是试图把球晃下来。我走进,用手推了推树——“蜻蜓摇柱,浮萍撼树”,这句话形容得如此贴切!我笑了笑,这树有四层楼高,怎么可能推得动。我四下张望,没人,大家都躲在阴凉处呢,我于是朝着树,小跳几步,然后对着树干就是一脚——树冠上的叶子摇曳几下,除了一些沙沙声,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又仔细地看看那个弹力球,它非常精确地卡在一个粗壮的三分叉上。我记得这球当时最高处是逼近树冠的,这么直直地落下来,又刚好卡在这么个位置,要是想用震动的方法摇下来,这力量估计能把树干折断——亦或是树被砍断,倒在地上了,这球可能还不出来呢!
在这里站得越久,我就被热得越躁动。我一只手拍打着衣服,想着别的法子弄下来。要不找个老师让他动用点资源?算了吧,都多大个人了还为着个弹力球兴师动众,老师答不答应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是真隔应。不过......我自己不会动用资源吗?我想起来了,来的路上有一个地方放着运动会要用的杂物,其中就有一把梯子。这个点估计工作人员都在运动会现场,我何不去借来一用呢。我赶紧往回跑去。
果然,一把长梯正靠在箱子上,没人守着,这简直是专门为我提供的嘛!拿吧,就算被问起来,就说有东西挂在树上,临时需要这个一用,想必他们也会同意的。
这梯子实在是长,我一个人扛着真的很费劲,才走几步路,我的汗就在脸上肆意地冒出来了;等我到了树下,后背已经湿了小半边。我把梯子靠在树上,梯子最高点刚好够到弹力球。我擦了擦手上的汗,爬上了梯子。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轻轻松松。可到了第五步,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梯子抖动得太厉害了。这大概是因为我架梯子时,倾斜角过大,加上我没有经验,身体太过紧张地发抖。我更加地握紧了梯子,但结果是抖动更大了。我顶着紧张,继续往上走一步,又是一步——
突然,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不安与恐惧,我的大脑来不及多想,手已经往前一伸,揪住了一根细细短短的枝芽,我的右手紧紧地拽着它,好歹稳定了平衡后,我才意识到,由于我摆梯子的危险角度,刚才我的重心变得非常靠后,险些失去平衡,向后栽倒。我现在的高度已经是一层楼高了,这要是摔倒了,加上梯子的重量......我立即后怕得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我把右脚慢慢地往下挪动,然后踩实了落脚点,这才让重心回到了安全的范围里。松开右手,指间落下一片被我薅下来的绿叶。若是刚刚这枝芽被我揪断了......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我赶快地回到了地面上。
等我两脚在地面上站稳了,我才发现自己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在颤抖。我看着自己的手,被血液充实得通红,甚至似乎感受到手随着我的心跳在抖动。我赶紧深呼吸几下,把心率降下来,晃了晃头,这才好去思考下一步怎么办。
很显然,我得把梯子更加倾斜一点,但我立刻想到,梯子的最高点也会随之降低,我可能得伸手才能够到它。我大致平复了一下心情,第二次上了梯子。
这下稳当多了。我一步一步地上去,很快就超过了一层楼的高度。我抬头向上看,弹力球离我还有一段距离。我继续向上爬。
或许我真的能成功,即便是现在,我也还是会后悔当时自己为什么要神经质地往下看一眼。我在离梯子最上一级还有两三步的时候,神差鬼使地往下看了一眼。那一瞬间,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离地面这么远过,而且,那地面离我的距离似乎还在越来越远,梯子在我眼里逐渐变细,细得似乎变成了一根钢筋——继而是钢丝一样的粗细。我此刻就好像悬在空中一样。我的腿开始颤栗,更可怕的是,他似乎是使不上力了。我眼前仿佛闪过几幕熟悉而悠久的回忆,那还是我蒙昧时期的记忆、孩提时代的噩梦——我这么就忘了我的恐高症呢!?
我僵在梯子上,一动不动,似乎连呼吸都忘了。我还在盯着地面,害怕得不敢移动。停了很久,我突然地吸进一大口气,然后很快地往下移动,在我的感觉里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我落在地面上,险些摔了一跤。
我头脑似乎是麻木了,半晌,我才回过神来,呆呆地看向那梯子,就算是我爬到梯子最上,以我的身高,估计也难够到。我又看了一会儿梯子,实在是没有勇气再上去了。还是决定把梯子还回去。
还回去的路上,梯子格外沉重,这也正常,我刚刚差点从上面摔下来两次,还能在这扛着个梯子走已经算好了。我归还了梯子:那里依旧没有人看守,然后又折回了树下。
此时,我的背上已经是湿透大半边了。那弹力球依旧在原处,一动不动。我静静地看着它,幻想着要是有一整风来,把它吹下来就好了。“想什么呢?”我自己笑自己,“你这么折腾它还不动,一阵风就能吹下来了?”
或许,来只鸟把它顺下来?我于是找哪里有鸟,耳朵确凿地听到有鸟叫,但是看不到哪里有鸟。我于是沿着路边仔细检查,果真在灌木丛下看见两只鸟,我就像见了救星一样赶过去,那两只鸟却一扇翅膀,扑棱一下飞走了,很快就化作了两个小黑点,消失在了视线里。
那要不,下一场雨也好啊,雨水或许能把弹力球冲刷下来。我又盼望着下雨。看向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云彩,只有一个耀眼的太阳,无情地刺痛着我的眼睛。现在是运动会期间,学校肯定是看准了这段时间不会有雨的。
我把视线从空中收回,继续看向那个弹力球,它在树杈间纹丝不动。它是在嘲讽我吗?亦或是责怪我把它丢在上面?
我就这样站在树下,时而发呆,时而思考,时而木愣地看着那个弹力球。我有没有在认真思考怎么把它取下来?我也不知道,我试想过的办法都没一个能行得通的。哪怕只是小如弹力球,想得到它,我一个人却束手无策。
我站在树下,全然忘了时间的流失,等我察觉到自己的脑袋似乎有点发晕时,我才明白,我不能再站在这太阳下暴晒了。
运动会几天后就结束了。这几天里,我总会在吃完饭后会教室的路上多拐个弯,去看一眼那个弹力球,每一次去,它都在那,没有一点变化。后来,下了几次大雨,它还在原处;大雪纷飞又消融,它还在原处;春天时百鸟争鸣,在各个树上搭建巢穴,它还在原处。我呢,每天总要去看它一眼,虽然我不能凭意念让它掉下来——对,我什么都做不了,除了就这么看着它。一年,两年过去了,树干在生长,它反而越陷越深。在春天繁盛的绿叶里,有时我找不到它的身影。秋天,片片落叶也会掩盖住它,让我一度以为它不在了,但过几天大风一吹,它还在原地,纹丝不动。
三年后,高考结束,我最后一次进入学校,最后一次去看那个弹力球。三年里,它除了随着树长高、更加紧密地嵌进树里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它还在那等着我去取,我也还是无能为力地看着,期望着不存在的奇迹。我看着这个在树中卡了三年的弹力球,心中无比的平静,也是无比的乏力。一阵风吹过,几片叶子掩盖住了它。“一时半会儿我是看不到它了的。”我这样想着。闭上眼,哪怕这三年来我看过它无数次,此刻却没有任何记忆浮现;连三年前,那次梯子上的惊心动魄,现在也只是一缕淡淡的轻烟了。
我睁开眼,转身向校门外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
拔出U盘,我把它放在手里细细端详:这U盘上满是细小的划痕,插头处磨损很大,想必是用了有些年头了。但里面的文件还能读取,说明还是能用的。
我把U盘放进桌子里,随后关上了抽屉。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