梗文化终于死在了笑声里(乐)
三,无趣
在互联网的公共场域里,越来越多的人以“玩梗”的方式表达立场,或逃避立场。这本来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表达方式,一种带有轻巧自嘲的幽默姿态。但当这种姿态成为人们面对一切尴尬、冲突乃至痛苦的默认反应,它便失去了原有的趣味,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防御机制。

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有人在严肃话题的评论区“希望是真的”,有人在他人叙述创伤经历时回复“是聊天记录,不得不信了”,还有人用一句“已经狗头保命了”来封住所有追问。更极端的是,当被指责不合时宜、不尊重时,他们会迅速退回一句熟悉的台词:“小学生带着你的正义感吃大份去吧”“不懂就别玩梗”。在这种语境下,玩梗者成了“上位者”,而质疑者反而成了“被审视”的那一方。

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有趣的权力结构,在传统的交流中,理解总被视为沟通的目标;而在当代互联网语境里,被误解反而成为一种防御。不被理解,意味着可以免于解释。于是,语言被故意制造成噪音,表达变成了一场伪装成游戏的逃避。
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玩梗式表达本身也映射出年轻群体的焦虑。他们知道自己身处一个情绪被放大的时代,一个“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集火”的舆论场。于是玩梗成了一种“去风险化”的表达方式,轻浮、模糊、可撤回。它让你参与公共话题的同时,始终保留退路:一旦被质疑,就可以说“我只是玩梗而已”。
这种语言游戏的后果,是现实经验的再度异化。一个原本承载情绪的表达被套上梗的模板,就像往一首歌里强行塞进流行节奏,(那一天的忧郁,忧郁起来)听起来熟悉,却没有任何感情。网络语汇越来越多,但真正能直达情绪的词却越来越少。我们说得越来越快,却听不见彼此。
最终,“玩梗”不再是沟通的方式,而是一种姿态。它让人显得机灵、独立、甚至显得不在乎。但同时,它也在一点点侵蚀人们面对真实的能力——我们习惯于笑,习惯于用笑抵抗悲伤,却早已忘了怎么去感受。
四,废墟
今天的梗文化,已经不是一场关于创意的游戏,而是一场关于速度的竞赛。每一个新梗的诞生都伴随着一场集体狂欢,但狂欢转瞬即逝。一个梗的生命周期,短得令人发笑——从出现、爆红、模仿、变形、滥用,到最终被弃置,往往不到二十四小时。信息流滚滚向前,旧梗被新梗掩埋,没有记忆,也不需要记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也是一种极度的虚无。因为当一切笑点都可以被算法生产,当每个人都能参与制造梗,幽默就不再需要创作,只需要传播。一个词,一个表情包,一段毫无意义的音频——只要循环足够多次,就能成为“新梗”。它们不需要灵感,不需要共情,只需要“复用率”。

更糟的是,这样的循环还在不断加速。那些原本带着自嘲意味的小圈子符号,被无休止地搬运到外部世界,在无数次断章取义中变形为粗暴的暗语。“魔怔圈”的出现,正是这种语言滥用的极端体现——一种将荒诞与自闭包装成文化的现象。人们在同一个词里互相识别,又在不同的语境里互相误解。语义成了游荡的幽灵,任何人都能给它赋予意义,也因此,它失去了意义。

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共鸣”也变得廉价。人们追逐的是笑点的“即时满足”,不是笑背后的思考。那些真正值得被讨论、被记住的内容,被淹没在重复与复读中。每个人都在讲梗,却没人再讲故事。

当代梗文化的荒谬之处,恰恰在于它的自我消解能力。它可以调侃任何事物,也可以轻易地调侃自己。于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被认真对待。连“认真”本身,都被视为异类
梗文化的衰败,不是因为我们不再有幽默感,而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语言的力量。语言原本是连接人和人、经验和经验的桥梁;而现在,它成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缓冲垫。我们用梗来表达,又用梗来抵消表达。笑声此起彼伏,却空洞得像背景噪音。
或许,这就是“后梗时代”的样子笑点依旧在生产,模板依旧在更新,流行依旧在循环。但当所有人都能发出声音时,真正的语言反而死去了。那座曾经充满创造力的互联网,如今像一片废墟。废墟上仍然有人在说笑,只是笑声再也传不出屏幕。
乐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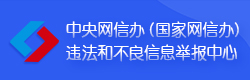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后梗时代逐渐变为一种以娱乐为载体的虚无民粹主义,这源于互联网等娱乐媒介对于情感而非理性的提倡,以及“后真相时代”中人们相对于真相更需要能够诉诸情感的片面事实的现象。
ma番号111111
怀念那个“马甲”的梗的时代,没那么多阴阳怪气,lzbd,兰州烧饼,囧等等等等![[family-6]](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2/无语.png)
┏┛┻━━━┛┻┓
┃|||||||┃
┃━ ┃
┃┳┛┗┳ ┃
┃ ┃
┃ ┻┃
┃ ┃
┗━┓┏━┛
┃史┃
┃诗┃
┃之┃
┃宠┃
┃ ┗━━━┓
┃经验与我同在┣┓
┃攻楼专用宠物┃
┗┓┓┏━┳┓┏┛
┃┫┫┃┫┫
┗┻┛┗┻┛
MA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