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光透过窗帘与墙壁之间的空隙射进屋内,在另一面墙上映出物品的阴影。上过蜡的木制地板上胡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我赤脚踏过翻开的书本,走到你的身边。你坐在椅子上,没有反应,睁开的双眼没有一丝生气和活力,如同人造的一般美丽而虚幻。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你我二人,目前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二人存在,这个房间之外的一切只有虚无。
我开始跪在你的脚下,双手颤抖地紧紧抓住你那放在腿上的白皙小手——啊,多么纤细,多么柔软!我的视线从握在手中的小手往上移向你的脸庞:软弹的皮肤,纹理十分独特;精致而又柔和的五官;真正让你远远超过世人的,是你那双晶莹剔透的天蓝色眼眸。
我的视线因为涌出的泪水而变得模糊;我低下了头,将你冰凉的手贴在我额头上。
我在此向你祈求、向你倾诉,因为你定能理解我的艰辛和困苦,并给予我安慰。
“……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理解我,不像在我生活中的那些俗物,只会用连他们自己都不懂的社会观念对我进行审判,把我判作没有价值和用处的废物。每天每日,在家里,在学校中,都要忍受别人轻蔑的视线。
“我的父母,其实只是跟我同住在一片屋檐下的陌生人,我跟他们起着作用的联系只能从法律和伦理中找到。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对我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苛求,要是我没有达成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摆着一张臭脸,不给我好脸色看;轻则只是辱骂、吼叫,重则就是体罚。在他们的管教下,我并不是作为自己,而是作为父母的欲望搅拌塑造而成的泥塑存在;我似乎生来就是在他们的人生游戏中满足他们的养成欲望。
“等到我初中确诊为抑郁症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再给我设立一些苛刻而难以达成的目标了,认定我是一个需要他们父母的亲情治愈心灵的精神病人。虽说他们对我比以前要好了,不过他们的武断却依旧不变;在这个家的生活依旧非常令人窒息。
“和一般的父母武断专横地为孩子所做的事一样,他们对我做的一切,对我的伤害,对我的侮辱,都能归结于“为我好”这个动机。他们自以为是心理医生,以为我只要“好好玩”,就能够治好抑郁症了;他们也不认为抑郁症是什么“正经的”病症,他们曾说这压根儿就不需要吃药。他们强硬地把我带到游乐场,设想出我只要在那些世俗的设施里游玩就能治好心理疾病的完美流程。在此期间,父母散发出的潜在的压力,令我不敢表现出对我父母安排的任何不满,只要在他们二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就不敢做出任何违抗。
“最近我休学在家,父母一致认定我将来没有出息,已经不对我抱有任何希望了,所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厉了。从出生起就一直和父母之间不可消除的矛盾,如今暂时缓和了,不过迟早有一天当我面对未来时,矛盾会又一次激化。”
我停了下来,抬起头再次注视着你的眼眸。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望向虚空——不是注视着我!你没有反应——不对,你只是克制住了自己感情的表露。因为我还没有说完,所以你保持沉默,等待我把话说完。
我继续说了下去:
“家庭生活再怎么恶劣,也不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患上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从初中开始的四年学校住宿生活才是把我的人生搅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那段经历,那么我也不会像现在那么消沉、颓废地窝在家里。
“学校宿舍中一间房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十个人,教室里则是五十多个人,像畜牲一样拥挤着,浑浑噩噩地接受学校的饲养。学生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活像是群将头伸出栏杆啃食食槽里的饲料的猪——这简直就是耻辱。这种耻辱、非人待遇,我忍受了整整四年。在那段时间,我找任何人倾诉,得到的只有他们的恶意的冷嘲热讽和丝毫不在意我的痛苦的斥责。我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话,是轻佻的‘受着呗’和傲慢的‘吃不了学习的苦,长大就吃生活的苦’。直到现在,我也只能对你诉苦。只有你才能理解我的感受。
“令我难以忍受的,不仅仅是学校自身所特有的压抑的氛围,而且还有同学和老师。他们联合对我这个不合群者的迫害……”
想到了直到高二休学前的那段学生时光,我一时语塞,只能无力地面对过去的幻像。你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不安的波浪渐渐涌上心头:你为什么还是缄默不言?你的手和你现在的态度一样冰冷。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年轻女人才不会嫌弃我,允许我触碰你的双手、你的身体,不像学校里的女学生那样。那些女人,碰到了她们的手,她们就像是碰到了脏东西一样,用触碰到的部位乱蹭周围的物体,还一脸恶心地大声向周围的人嚷道:‘我的手被他碰到,不干净了!’表现最严重的,还是初二跟我同班的嘉怡,好心给她捡起她掉到地板上的橡皮,结果她当众羞辱我,两指掐着橡皮丢到了垃圾桶里。那群雌兽这般嫌弃我,只是因为我相貌丑陋,平时看到了我的脸,就说她们的眼睛脏了……
“而男生跟那群女生一样在内心无比嫌弃我的存在。一般我都是他们开玩笑和恶作剧的对象,在教室中以我为嘲笑对象跟女生们一应一合。在宿舍里,当舍友们价格高昂的球鞋脏了,他们就轮流用我洗脸和擦身子的毛巾擦鞋,擦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当我回宿舍看到他们的行为后,难以抑制住愤怒地边大声吼叫边冲向他们所在的阳台,他们将毛巾丢到我的脸上,趁我还没做出反应就绕到我的背后踹了我一脚,欢笑着溜出阳台,把阳台的玻璃推拉门锁上了。我只能一边任悔恨的泪水流下,一边在盥洗台上拼命搓洗满是污迹的毛巾,最后也没能洗干净,只能丢到垃圾桶里。
“老师完全无法处理同学对我的歧视。跟老师沟通,最多也只是换宿舍和换班,或者是让那帮人收敛一点,他们还是一样继续侮辱、嘲讽我。而且老师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处理公事,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对老师们来说,只要事情不闹大,怎样都行,以一种理性的冷酷的口吻劝我要熬过那初中三年,争取考个好成绩,上个好高中摆脱那些不良学生……我知道,他们要的是指标,要的是成绩优异的学生。
“因为我上的初中是价格高昂的私立学校,父母舍不得早已缴纳的三年学费,所以不顾我想要转学的要求,逼我要在那里读完三年。
“我资质平平,学习成绩一般,也没有什么爱好和特长,而且身材矮小瘦弱,最后上了一个普通高中。那所高中虽然还是如同圈养人一般的寄宿制,不过像初中同学一样歧视我的人倒是没有了……虽说如此,可我再也无法忍受学校的存在了。在高一的那段时间,我仿佛成了一个机器,每天的生话是机械而僵死的——这也叫作规律——我的感觉处于失真的状态,好像我的身体没有稳固的支点,以至于所有的行为都显得很软弱无力。
“虽然我现在只是休学一年,但是现在我完全不敢想象自己明年回学校复学……或许我父母是对的,根本就不敢回学校的我,就不可能会有出息。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从来都不是人,而只是一种被抽象的身份决定的符号。在父母看来,我只是儿子这个身份的复制品;在学校和老师看来,我只是学生这个身份的复制品。我的本质是他人的欲望混合而成的。我这个被社会造来用于机器运作的齿轮残破不堪。”
你为什么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样子,我只是想得到你的安慰,哪怕是这么微小的愿望,你都不肯实现吗?
我的双手鲁莽地伸向了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折断了似的垂了下来,如人偶一般毫无生气。不管我再怎么自欺欺人,也无法掩盖这个事实:以我的恋人的身份,被囚禁在这个房间里的你,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我的欲望杂糅而成的理想形象。你是人造的玩偶或是没有意识的空壳,却唯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然你早已弃我而去了。
把你的头扶了起来,那双空虚的眼睛永远也不会看向我。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可实际上,我和他们是一丘之貉,我在内心中也是非常认同他们把人抽象化的做法的。我一边控诉他们对我人格的抽象化和符号化,一边同时也用空洞的抽象概念取代他们的真实存在。我把你当成自己的泄欲工具,还一厢情愿地以为你爱着我。
“当你还只是我拙劣的画作时,我和其他人一样轻浮地称呼你为‘纸片人’;当你的肉体被造成时,你在‘老婆’的名号下却遭到妓女的待遇……因为是虚构的,所以就觉得你低人一等,在想象中和行为上就不把你当成一个拥有灵魂的独立个体——我爱的人真是你吗?我真的配爱你吗?”
虚构的幻想世界正破裂碎散开来,其碎片如打碎的玻璃般残留在现实之中。现在已经没有你了,有的只是一个做工精细的人偶。同时我的内心也暴露在许久未见的恐怖现实之中,没有了幻想的保护。
梦在我犯下的恶行下崩溃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将来了。如果我真的知错,要对得起你,就不能再逃回梦境了。可是,我能在现实中活下来吗?
我离开了你——准确地说,是人偶,是为我的欲望而生的空壳。走到房门前,我战战兢兢地握住冰冷的门把手。即使我忍受不了现实而选择自尽,我也必须打开房门,接触外界。
打开门,一阵清凉的风吹了进来,一道耀眼的光芒照射进来。我转身看向昏暗的室内,看向了你——我还是忘不了你。即使只是个空壳,我也不敢看着你的眼睛。沉重的叹息,视线转向前方。我踏出了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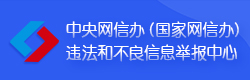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差点没认出是你![[stick-1]](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new/喵隐-呆.png)
![[family-4]](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2/诶嘿.png)
铃仙换头像了![[stick-1]](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new/喵隐-呆.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