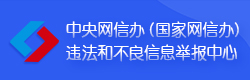北国的冬,我记忆中的故乡的冬,总是静静地来,又悄悄地走。当你在忽然而起的风中打个冷颤,才会意识到,原来已经入冬了啊;同样地,只有你穿着棉衣在明媚的阳光下汗流浃背时,才猛地觉察出来,冬已在你不知不觉间悄然离开了。
我的儿时记忆中,与冬相关的部分大概是天未亮的清晨。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自己走路上下学,到能够骑车时是在初二左右,那时的我才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山地自行车,我们这管它叫“大赛”;而截至那之前,我便不得不走路,靠着自己的双腿支起沉重的书包。
自家中出发约是在五点半,天还完全没有要亮的意思,它比我仍在酣睡的父母起的还要晚。但不至于无光。都说黎明前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可并非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在我印象中的冬天的清晨,月亮还挂在空中呢,甚至于在白天也能看到月亮的,是日月同辉的奇妙景象。我并不知晓这是否是常见的天象,但对于我很常见,甚至是在我撰写这篇随笔的今天,也是一整天都能看得到月亮,只是在中午不见——不知道是太阳的灼目的光掩盖了月的辉芒,还是月儿实在疲惫偷偷落下去小憩了一会儿。
小区里有家包子铺,一块钱一个大包子,两块钱我就能吃饱,于是在父母懒得起床做早饭的情况下,——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学日在家吃早饭的经历鲜少——在鞋柜上专门放零钱的旧药瓶中拣出两枚硬币,绕一点远路到那个包子铺去买上两个包子做早饭,肉馅或者小白菜馅。
天是在我边走路边吃包子时亮起来的。先是一边的天空亮起一片蓝色,说“亮起”其实不准确,在我看来,夜晚的天空像是涂了一层重重的蓝色墨水,一层又一层,蓝色覆盖上蓝色,深邃了,便显得漆黑无比;而那黎明的天光的出现,像是在天的帷幕的一侧蓦地点上一滴清水,于是那墨稀释了,淡化了,便呈现了由黑到深蓝到浅蓝的浑厚的渐变色,那颜色是我教了十多年水彩的美术老师都不遑论能够复刻得分毫不差的。
于是天渐渐明朗了,阳光的轮廓被这渐变的天蓝色半轮标记出,渐渐地扩大,扩大,重复向那一个位置不断滴加着清水,最终洗去了一片天空的墨染,显露出蔚蓝的明亮的底色来,紧接着那轮火红便挤出地平线来,不厌其烦地观察他已见过千百遍的世界。
若是走的快,一般在我快到学校时刚好能见到朝阳;若是路上贪玩耽误了些许时辰,便只能追在他后面匆匆地跑了。
说回到冬来,或许世人对于冬最惯常的字眼便是雪了。雪是冬的精灵,洁白,无暇,总能引起人们的向往。我对北国的雪曾经也是抱有满心欢喜的;犹记我儿时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雪下了一夜,晨时便能到我脚脖子深,学校还因这突然的大雪突然地放了两天假。自不必说,打雪仗,堆雪人是必备节目,但我比较文静,不喜打闹,本身自幼也并无玩伴,于是尝试跟母亲一起堆雪人。路面脏兮兮的,雪人也脏兮兮的,我听母亲高兴的讲述她童年时的玩雪经历,再看看面前黑煤球一样的雪人,没有手臂——小区不让折损树木,没有五官——母亲不许我浪费胡萝卜或者纽扣,更没有帽子和围巾——且不说母亲绝对不会允许我弄脏他们,就是说我们家也根本也没有这两件事物。
自那之后,我忽地对北国的雪失去了好感。我依然喜欢看雪纷纷扬扬地下,铺盖得世界银装素裹;但我却无论如何都对玩雪提不起兴趣了。雪太容易被弄脏了,也太容易弄脏别人了。
我记忆中北国的冬,是由凛冽的,带着灰尘与煤烟的风组成的。冬天总是会起大风,春天也是,秋天也是,唯独最需要风的夏天却不见其一点踪迹。我喜欢打羽毛球,但却很难寻到故国无风的清宁日子。
冬天的风是很坏的。自从冬季的雪越来越少,甚至几乎消失不见,地面上久积的沙尘便猖狂起来,借由风的威势满天满地地肆虐。在这样的日子出门可要当心!稍不留神便会被风扑了满脸灰尘,风打在脸上是疼的,土落进嘴里是苦的。我自幼不喜外出,大概这风要占一半的功劳的。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北国的冬是在不断消逝的。似乎是因为燃煤,全球变暖或是其它的什么科学现象,北国的冬,故乡的冬,一年比一年迟到,却一年比一年早退。
北国的冬,我记忆中的故乡的冬,却在一年一年地渐行渐远了。无论我多么厌烦冬日毫不客气的种种事物,终归还是有温暖的记忆留存的。于是看着本来漫长的严寒的冬,带着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种种美好渐渐消逝时,我的心中竟也产生了不舍。我怀念那水彩画般的日出图景,怀念小区里的包子铺,怀念冬日打羽毛球到处追着球跑的傻样,怀念玩雪时母亲童心未泯的快乐的笑容。可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那凛冽的北风,越飞越远了,渐渐地淡出我的视野了。只剩了肮脏泥泞的冰雪,漫天飞扬的灰尘,和高大烟囱不断给与天空的废气。故乡的冬,似乎只有人依旧存留着温暖了。
北国的冬,我记忆中的冬,渐行渐远的故乡的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