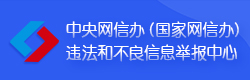真仪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门轴发出一声“吱嘎”长音。
楼道里的空气并没有比屋子里好多少,对于习惯了海风那种通透味道的真仪来说,这种“城市里的空气”简直像是一团黏糊糊的湿抹布捂在了脸上。
“哎呀呀!咳咳!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伊果立刻遭了殃。
她那原本在空中扑扇得欢快的单翼猛地一僵,整个人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臭气墙。她用两根手指死死捏住那个精致的小鼻子,脸蛋憋得通红,在空中夸张地扭动着身子,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外面这味儿怎么比里面还冲!我说小真真,你这是要把本大人带到哪个垃圾堆去进膳吗?你就不能找个像样点儿的地方?比如那种……”
她在空中转了个圈,金色长发甩出一道流光,小手比划出一个拱门形状。
“那种亮晶晶的!门口铺着红地毯,一进去就有那种穿着黑衣服、把腰弯成九十度的人齐声喊‘欢迎光临’的地方!那种地方的空气肯定是香的!”
真仪连头都没回,锁好门,迈步向楼梯走去。
“莫得钱。”
“钱?钱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伊果见真仪不理她,立刻飞到真仪面前,双手叉腰,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你想想办法嘛!你是谁啊?你可是那个……那个……”
伊果卡壳了一下,她那漫长的记忆里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形容眼前这个落魄的少女。最后,她只能含糊其辞地挥了挥手。
“反正你很厉害就是了!没钱就去拿嘛!你看那边!”
她的小手胡乱指向远处。透过楼道尽头那扇满是灰尘的窗户,依然能看到碧海市中心那片璀璨夺目的灯火。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像是一根根由光构成的水晶柱,刺破了夜空。
“去那个亮闪闪的大楼里!那里肯定堆满了金子和好吃的!你就进去,随手拿一点,谁敢拦你?”
真仪停下脚步,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教唆犯罪的“神明”。
“偷东西要挨抓,刚出来,不想再进去咯。”
“抓?哈!”
伊果在空中做了一个极不屑的后空翻,裙摆飞扬。
“谁敢抓你?那些凡人?打趴他们不就好了!就像你以前……以前那样!”
“闭嘴。”
真仪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
她绕过伊果,顺着那水泥楼梯快步走下去。她的肚子已经在抗议了,胃壁摩擦发出的声响在这安静的楼道里清晰可闻。
走出青叶团地那压抑的阴影,外面的世界稍微喧闹了一些。
路灯已经亮了起来。那是老式的钠光灯,散发着昏黄且容易招虫子的光线。无数细小的飞虫正围着灯泡不知疲倦地嗡嗡乱撞,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真仪沿着来时的路,走进了那条略显萧条的商店街。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这里并没有变得冷清,反而因为夜色的掩护,透出一种白日里没有的活力。
一阵极其霸道的香气猛地钻进了鼻孔,那是油脂与淀粉发生剧烈反应后产生的味道。
路边那家并没有招牌的炸物店还在营业,昏黄的灯泡下一口巨大的油锅正翻滚着金色的波浪。
老板娘正拿着长长的筷子,从油锅里捞出一块块炸得金黄酥脆的肉饼和鸡块。
“滋啦——”
那是食物出锅时美妙的声响。
伊果的小鼻子猛地抽动了两下,就像是猎犬嗅到了猎物。下一秒,她那一双碧绿的大眼睛“唰”地一下亮了。
“哇!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好!这就是凡人的智慧吗!小真真!快!过来这边!”
她完全忘记了刚才还在抱怨空气难闻,没心没肺地冲向了炸物店。
真仪的脚步不受控制地顿了一下。
那是身体最本能的反应。长途跋涉后的饥饿感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她看着伊果兴奋地围着那个满是油垢的玻璃柜台打转。
老板娘正忙着给一位穿着工装的大叔装一袋热气腾腾的炸土豆饼,根本没注意到空中这个发光的小不点。
“老板!这个!这个圆滚滚的!还有这个长条的!哇,那个好多脚的是什么?鱿鱼吗?对对对!就是那个!全都给本大人来一份!要最大份的!还要多撒点那种红红的粉!”
伊果站在油腻腻的柜台边缘,踮着脚尖,小手豪气干云地指指点点,仿佛她真的能掏出钱来买单一样。
真仪咽了一口口水,强迫自己的视线从那块还在滋滋冒油的炸猪排上移开。她走过去,面无表情地伸出手,一把揪住伊果背后的衣服领子,把她像拎小鸡仔一样拎了回来。
“莫闹。”
“哎呦!你干嘛呀!放手!放手!本大人的炸鱿鱼,本大人的炸猪排!”
伊果在真仪的手里拼命挣扎,两条小短腿在空中乱蹬,翅膀扑腾得像只被网住的扑棱蛾子。
“闻着这么香!那金黄色的色泽,那清脆的声音……这是艺术品啊!买嘛买嘛!本大人命令你买!我是神!神谕你懂不懂,不肖小真真还不快点跪下接旨!”
真仪没有理会她的叫嚣。她的目光快速地扫过了玻璃柜旁那个手写的价格牌。
炸鸡块(5个)——300円。
炸猪肉饼——180円。
炸鱿鱼脚——250円。
她的手伸进口袋倒腾了两下,只有几枚可怜的硬币在叮当作响,那是除了那一沓整钱之外,她身上仅剩的零碎。
一百,五十,十……
加起来不到四百円。
如果买了炸鸡,明天的早饭就没有着落了。如果买了猪肉饼,那渴了压根就买不起水喝。
她把那几枚硬币捏紧,然后把还在大喊大叫的伊果一把揣进了自己卫衣的口袋里。
“不吃这个。”
“为什么不吃!你有钱!我刚才都听见响了!”
伊果的小脑袋顽强地从口袋边缘冒出来,金发乱蓬蓬的,脸颊气鼓鼓得像个河豚。
“小气鬼!喝凉水!你刚才给那个地中海房东一大把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给本大人买口吃的你就装穷!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啊——!”
“说些背时话,我不交房租我睡大街切。”
真仪按住她的脑袋,把她摁回去。
“那……那去吃那边!”
伊果显然不打算放弃。她在真仪的口袋里不安分地扭动,像条毛毛虫。
她伸出一根小手指,指向街道对面一家亮着暖黄色灯笼的小店——
【豚珍亭·豚骨拉面定食】
浓郁的骨汤味飘了过来。
“也贵。一碗面要六百。”
真仪看都不用看,那个价格在进这条街的时候她就扫过了。
“那……那个!那个总行了吧!那个看起来很破!肯定便宜!”
伊果指向街角一家只能站着吃的小铺子,灯牌上写着“立食乌龙”四个大字。门口站着两个刚下班的建筑工人,正端着大碗,呼呼地吸溜着面条,热气腾腾。
真仪这次停下了脚步。
乌龙面,小碗,250円。
这个价格……咬咬牙,似乎是可以的。
那清亮的汤底,漂浮的葱花,还有那吸饱了汤汁的油豆腐……
她站在路灯的阴影里,犹豫了整整五秒钟。
只要走进去,就能喝上一口热汤。
但是……如果不买制服,就没法上学。不上学,奶奶的钱就白花了。如果不省下每一分钱,那个天文数字般的二十万八千円要攒到什么时候?
“……算了。”
最终,真仪还是低下了头,重新迈开了脚步,从“立食乌龙”那温暖的蒸汽旁走了过去。
口袋里传来了伊果绝望的哀鸣。
“细川真仪造反啦!本大人要饿死了!神陨了你要负责!你要遭天谴的——!”
真仪充耳不闻。她把手插在兜里,低着头,继续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这条街并不长,但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却像是走不到尽头。
她的目光掠过那些明亮的橱窗。
一家精品店里陈列着那种蕾丝边的洋装,标价是一万二千円。那是她两个月的房租。
一家面包房刚刚烤好了一炉牛角包,浓郁的黄油香气简直是犯罪。
一家杂货铺里摆满了那种亮闪闪的小饰物,一群穿着校服的女学生正围在那里叽叽喳喳地挑选。
这些都与她无关。
她就像是一个幽灵,游荡在这个充满了物欲和食欲的世界里,却无法触碰任何东西。
“诶!小真真!你看那个大叔的胡子好搞笑,白的一坨!”
“哇,那件衣服亮闪闪的!唔……本大人的眼睛好闪!虽然品味差了点,但上面的亮片如果抠下来给本大人做头饰好像也不错……”
“快看快看!那只狗好胖!它是猪吗?嘻嘻,好想上去踹他一脚的说,看能不能滚起来。”
虽然真仪已经尽力无视她了,但伊果并没有因为没吃到东西而消停。她似乎把这种“喋喋不休”当成了对真仪的惩罚,不停地在大惊小怪,试图引起真仪的注意,或者单纯就是为了发泄不满。
直到真仪走到商店街中段,一个不太起眼的拐角。
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一家超市的门脸出现在眼前。
它不像前面的店铺那样光鲜亮丽,白色的日光灯管有一根还在不停闪烁。门口挂着透明的防风帘,有些发黄。
红色的喇叭挂在门框上,里面传来机械单调的循环广播:
“……玉田市场……今日特价……临期商品大甩卖……安心……便宜……主妇的好帮手……”
门口摆着几个蓝色的塑料筐,里面堆着一些因为长相歪瓜裂枣而被捆在一起打折销售的蔬菜。几根带着泥的大葱,几个表皮有点皱的苹果。
“玉田市场……”
真仪看着招牌上那几个有些褪色的红字,低声念了一遍。
“便宜”两个字,像是带着某种魔力,勾住了她的脚。
“诶?来这里干嘛?”
伊果好奇地从口袋里飞了出来,落在了一捆打折的大葱上。她嫌弃地看了一眼那个满是泥土的葱根,小鼻子皱了皱,又飞了起来。
“这里的味道好奇怪哦……一股土味,没有刚才香!小真真,你不会是想带本大人来吃草吧?本大人可是不吃素的!”
真仪没理会伊果的点评,她深吸一口气,掀开那沉重的塑料门帘走了进去。
超市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拥挤。货架摆放得密密麻麻,过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生鲜区特有的腥味和冷气的味道。
真仪推了一辆有些跑偏的小推车,开始在货架间穿梭。
她是带着目的来的。
在九州老家吃饭讲究个“味儿”。海风吹大的人,嘴里没点咸味、辣味是活不下去的。
她想找点像样的东西。比如那种红彤彤的,裹满了辣椒面的明太子,或者是一罐咸得能让人眯起眼的腌海带,再不济,那种加了蒜的拉面调料包也行。
但是随着她在货架间越走越深,她的眉头也越皱越紧。
这城里的超市东西倒是不少,包装也都花花绿绿的挺好看,可仔细一看……
那所谓的“辣味”咖喱,包装上画着火焰,配料表里辣椒却排在最后面,看着就一股子腻味。
那种标着“激辛”的零食在她看来估计连给舌头挠痒痒都不够。
至于咸菜更是让她大失所望。
那些腌萝卜腌黄瓜一个个颜色鲜艳得不正常,全是糖精和色素堆出来的。那种老家坛子里腌出来的黑乎乎的酱菜,这里根本没有踪影。
“这城里人……都没长舌头吗?”
真仪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
“咋个吃的都这么淡?嘴里淡出个鸟来。”
“就是就是!”
伊果坐在推车的把手上,附和地点头。
“本大人也觉得!这些东西看着就没劲!一点灵魂都没有!小真真,我们要不去那边看看?那边画着肉诶!”
真仪叹了口气,推着车径直走向了靠里的熟食区。
那是超市每天晚上最热闹,也是最残酷的战场。
一个很大的开放式冷藏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便当和熟食。
就在几分钟前,店员刚刚拿着打折机走过这里。那“啪嗒啪嗒”贴标签的声音,在某些人听来简直就是天籁。
一群大妈和刚下班的社畜正围在那里,眼疾手快地抢夺着贴了半价标签的炸猪排饭和汉堡肉便当。
真仪没有那个体力去挤,也不想去挤。
她站在外围,等到人群散去了一些,才慢慢走过去。
那些看起来丰盛、有肉有菜的便当,即便贴了打折标,价格依然在398円、298円左右。对现在的她来说,还是太奢侈了。
她的目光在冷柜里搜寻着,最终停留在最角落、无人问津的一个格子里。
那里孤零零地躺着几个白色的发泡塑料盒。上面的标签不是黄色的“20%OFF”,也不是红色的“半价”,而是直接手写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低价。
【特惠!日之丸便当——150円】
真仪伸出手,拿起一盒。
那个塑料盒轻得可怜,透过透明的盖子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内容,简单得令人发指:
满满的一大坨压得实实的白米饭。
而在这一片苍茫的白色正中间,孤零零地放着一颗深红色的腌梅干。
除此之外没有一片菜叶,没有一滴肉汁,甚至连一点点芝麻都没有洒。
白色的米饭,红色的梅干。
就像是一面日本国旗。
真仪拿着这盒便当盯着那颗梅干看了一会儿。
150円。
这可能是这座城市里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一顿饱饭了。
“就它了。”
她把便当放进空荡荡的推车里,又转身去旁边的饮料柜。她在那些花哨的果汁和汽水之间扫视了一圈,最后拿了一瓶最便宜的无糖乌龙茶(98円)。
走到收银台。
收银员是个没什么表情的中年大叔,发际线有点高,眼神疲惫。他机械地拿起便当,扫码,又拿起茶,扫码。
“一共248円。”
真仪从裤兜里掏出那几枚硬币在柜台上仔细地数了数,正好凑齐。
大叔麻利地收钱,把东西装进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递了过来。
“谢谢光临。”
真仪拎起那个轻飘飘的塑料袋,伊果立刻飞过来,扒着袋子口往里张望。
当她看清那盒便当的真面目时,那张精致的小脸瞬间垮了下来。
“有没有搞错小真真!咱们就……就吃这个?这算什么嘛!一个冷冰冰的饭坨坨,加一颗皱巴巴的酸梅子?这玩意儿能吃?这是给人吃的吗?喂喂!小真真!你这是在看不起本大人吗?基本神权你懂不懂?本大人好歹也算个……”
真仪没有理会她的抗议,拎着袋子转身走出了超市。
外面的夜色更深了。
伊果这次是真的受了打击,大概是对那寒酸的便当彻底绝望了。回去的路上,她也不再嚷嚷着要吃这要吃那,只是蔫蔫地坐在真仪的肩膀上,两只小手紧紧抓着真仪的一缕头发保持平衡,随着真仪的步伐一晃一晃的,偶尔发出一两声充满怨念的哼哼。
穿过那条堆着纸箱的小胡同,重新回到青叶团地那片压抑的楼群下。
楼道里的感应灯依然没亮,晚上根本就是直接摸黑。
真仪爬上四楼,用钥匙打开那扇深绿色的铁门。
“嘎吱——”
屋子里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空荡冰冷,没有任何人气。只有窗外远处那片璀璨的光带透过脏兮兮的玻璃窗投射进来,在地板上拉出几条微弱的光迹。
真仪关上门,打开那盏昏黄的吊灯,赤脚踩在冰冷的榻榻米上。脚底传来的凉意让她稍微清醒了一些。
她走到房间中央那个唯一的家具——那张矮腿的小方桌前,盘腿坐下。
塑料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把那盒“日之丸便当”和乌龙茶拿出来,摆在桌上。
拧开饮料瓶,仰头喝了一口,冰冷的茶水带着一点苦涩的味道滑过喉咙。
还算安逸,正好她也渴了。
然后她伸手揭开了便当盒的盖子,一股冷饭的馊味飘了出来。真仪掰开那双一次性筷子,相互刮了刮上面的毛刺。
“我要开动了。”
她低声念了一句,虽然这里并没有人听。
筷子插进有些板结的米饭里,挖起一大块,送进嘴里。
冷硬,干涩,没有什么米香味,只有纯粹的淀粉口感。
她咀嚼着,眼神有些恍惚。
看着这盒寒酸得不能再寒酸的便当,一段久远的记忆突然涌上了心头。
那是很久以前,奶奶还没这么老,腰也没弯得这么厉害。
夏天的晚上蚊子很多,奶奶一边摇着蒲扇给她赶蚊子,一边给她讲以前的故事。
讲昭和时候,讲那场把所有人都卷进去的战争。
“幺妹,那时候真是造孽哦。”
“昭和十九年的时候太平洋上打仗,年景不好,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海里打上来的鱼我们都不能自家吃,都要交上去劳军,给那些丘八吃。谁要是敢私藏一条鱼,那是非国民,要被抓去游街的。”
“我们这些渔民,守着大海没鱼吃。地里的庄稼也不行。那时候大家都吃什么?都是吃掺了糠的橡子粥,吃红薯渣子。那些批玩意剌嗓子啊,咽都咽不下去。”
“那时候要是能吃上一口精白米做的饭,那就是过年了,就是享福了。哪敢想什么菜啊肉啊的。只要有一碗白米饭,哪怕是光着吃都安逸得很。”
真仪看着眼前的这盒饭。在奶奶的故事里,这是只有过节才能吃到的“银舍利”。
“享福了啊……”
真仪低声嘟囔了一句。
她夹起一点点梅干肉,放进嘴里。
一股、直冲天灵盖的酸咸味瞬间在舌尖炸开,刺激得两颊生津。
她赶紧扒了一大口白饭。
那股酸味混合着米饭的甜味,在口腔里中和,虽然粗糙,却莫名地让人觉得踏实。
这就是活着的味道。
伊果一直抱着胳膊,气鼓鼓地悬浮在便当盒上方,居高临下地看着真仪吃这种“猪食”。看了一会儿,她大概是实在受不了这沉默和寒酸的气氛,也可能是那颗红通通的梅干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什么高级水果。
“喂……”
她小心翼翼地降落在桌边,凑近那颗梅干,戳了戳皱巴巴的表面。
“真的……只有这个啊?看起来……颜色倒是不错。这玩意儿……好吃吗?”
真仪没说话,只是用筷子夹了一点点沾着梅肉的饭粒,递到她面前。
伊果半信半疑地看着那一小团饭。她咽了口口水,本着“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伸着脖子,就像一只小猫一样,就着真仪的手,小小地咬了一点点。
下一秒——
“噗!!!”
伊果那张精致的小脸瞬间皱成了一团,五官都挤在了一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呸呸呸!呸呸呸!”
她猛地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小手在嘴边拼命地扇风,整个人在桌子上蹦了起来。
“好酸!!!好咸!!!这是什么生化武器!这什么怪味道!舌头!本大人的舌头要掉了!”
她惨叫着,冲到真仪的茶瓶边,抱着那巨大的瓶口想要喝水,却差点掉进去。
“难吃死了!这是毒药吧!绝对是毒药!小真真你怎么吃得下去的!你的舌头一定是坏了吧!”
真仪看着她那副狼狈样,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批娃嘞,这就是梅干,好东西的嘛。”
“好东西个鬼!这是谋杀!”
伊果眼泪都要酸出来了,她飞回到桌角,抱着膝盖缩成一团,一脸幽怨地看着真仪。
“你们凡人……真是太可怕了……”
真仪没再理她,继续低下头。
一口米饭,一点梅干。
虽然难吃,虽然寒酸,但胃里那种空虚的灼烧感正在一点点消退。
对她这种在渔船上干过活,吃惯了那种为了补充盐分而腌得死咸的鱼干的人来说,这梅干虽然酸了点,但也只能算是个开胃的零嘴。相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城里菜,这种直来直去的味道反而更对她的胃口。
她一口一口把那一大盒白饭和那颗让伊果闻风丧胆的酸梅干全部吃得干干净净。连盖子上粘着的几粒米,也被她用筷子仔细地刮下来吃掉了。
吃完最后一口,真仪把空便当盒盖好,仰头把剩下的乌龙茶喝光。
“呼……”
她长出了一口气。
饱了。
虽然只是碳水化合物带来的饱腹感,但也足够支撑到明天了。
吃饱了,身上那股子黏腻的不适感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坐船,坐车,又走了那么久的路,出了好几身汗。那件宽大的T恤贴在背上,感觉像是长了一层霉菌。
“我要洗澡。”
真仪站起身,收拾掉桌上的垃圾。
“洗澡?哼,去洗吧去洗吧,把你那一身穷酸味洗掉!”
伊果还在为刚才那口梅干耿耿于怀,没好气地挥了挥手。
真仪拿上毛巾和换洗的内衣,走进了玄关旁边那个狭小的浴室。
真的很小。浴缸大概只有半米长,那是给小孩子准备的吧?成年人坐进去估计只能抱着膝盖。
不过只要有热水就好。
真仪关上门,脱掉衣服,打开了淋浴喷头。
没有水。
她愣了一下,扭头看向墙上那个看起来有些年头,带着投币口的灰色铁盒子。
“啧。”
真仪皱了皱眉。这种老古董她在佐世保都没怎么见过,没想到在这大城市里还能碰上。
她无奈地擦干手,从脱下来的裤兜里摸出剩下的那几枚硬币。
一百円。
按那个快被水渍糊得看不清的标签上的字来看,一百円应该能洗个十分钟左右。
她把那枚一百円硬币塞进投币口。
“哐当。”
一声清脆的响声,硬币落进去了。
真仪看着那个红色的指示灯。
一秒。
两秒。
三秒。
灯没亮。
也没有听到燃气点火那种“噗”的声音。
“啥子情况?”
真仪拍了拍那个铁盒子。
没反应。
她又用力拍了两下。
“哐!哐!”
铁盒子纹丝不动,像是一个吞了钱就装死的无赖。
“不是吧……”
真仪有点慌了。那是她仅剩的几枚硬币之一啊。
她又不信邪地摸出一枚十円的硬币,塞了进去。
“哐当。”
依然没反应。
指示灯依旧黑着,水龙头里依旧流不出热水。
“麻买批……要爪子哦。”
这破机器坏了?还是说这里的规矩不一样?
她试着拧开水龙头。
“哗啦——”
水倒是出来了。
但是,刺骨的冰凉。
现在已经是四月末了,虽然不是寒冬腊月,但也绝对称不上温柔。
真仪的手伸进去试了一下,立刻缩了回来。
凉得透心。
她站在狭窄的浴室里,赤着身子,看着那个吞了她一百一十円却毫无反应的铁盒子陷入了沉思。
还要再投吗?
手里只剩下最后几十円了。如果再被吞了,明天坐车的钱都不够了。
可是不洗……身上真的很难受。
“……算了。”
真仪咬了咬牙。
她是海边长大的,冬天跳进海里捞鱼也是常有的事。这点冷水算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猛地拧开了水龙头,把喷头举过头顶。
“嘶——!!!”
冰冷的水柱浇下来的瞬间,她还是没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的皮肤瞬间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冷。
真冷。
像是无数根针扎在身上。
她咬着牙快速地搓洗着身体,尽量不让冷水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哈哈哈哈!小真真你在干嘛?学和尚练功吗?”
浴室门外传来了伊果幸灾乐祸的笑声。
“哇!这水看着就好冷!你的嘴唇都紫了诶!这就是凡人的修行吗?太有趣了!”
“闭嘴!”
真仪哆哆嗦嗦地吼了一句,抓起肥皂胡乱抹了两下,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冲掉泡沫。
大概不到三分钟。
当她关上水龙头,用毛巾裹住身体冲出浴室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刚从冰窖里爬出来。
“阿嚏!”
她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赶紧抓起件外套套在身上。
屋子里一时陷入了沉默。只有伊果身上散发出的微弱金光在昏暗的灯泡下闪烁着。
“喂……小真真……”
伊果飘在半空中,看着真仪还在微微发抖的肩膀,语气难得软了一点点。
“明天……你真的就要这个样子去那个……学校?”
她挥着小手,比划了一下真仪身上那套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
“就穿这个?会被笑话死的吧?那些贵族学校的人,可是很势利的哦。”
真仪收拾包装盒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抬眼看了看被扔在榻榻米角落的那张制服采购单。
那上面的数字依然刺眼。
“不然咋子办嘛。”
她低下头,继续收拾。
“先去了再说。总不能不去,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的嘛。”
“可是……”
“没可是。”
真仪把塑料袋打了个结,随手放在门边。她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回那个硕大的背包。
“啧。”
她用力把背包拖到榻榻米中央,拉链刺啦一声被扯开,里面那点可怜的家当一览无余——
几件叠得还算整齐但明显旧了的换洗衣物,颜色非灰即黑,;一双鞋底都快磨平了的备用运动鞋;一个边缘开裂的塑料漱口杯,里面塞着牙刷和一支快挤完的牙膏;还有几本从少年院带出来的封皮都掉了的书。
这就是她的全部身家。
她蹲下身,开始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掏。
“哎呀!这是什么呀!”
伊果也凑了过来,似乎对“整理”这项活动很感兴趣。她飞到那堆衣服上方,伸出小手拎起一件灰色的T恤。
“这颜色也太丑了吧!像老鼠皮一样!还有这个破洞……”
说着,她随手把那件T恤往旁边一扔。
“这件裤子也是!又肥又大,毫无版型可言!扔掉扔掉!”
她像个挑剔的造型师,一边评头论足,一边把真仪刚拿出来的衣服胡乱地往四周扔。
真仪刚叠好一件,伊果就弄乱两件。
“你搞啥子!”
真仪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伊果的翅膀把她拎到一边。
“别捣乱!再乱扔滚出去!”
“哼!本大人是在帮你筛选!这些垃圾根本配不上本大人的随从!”
伊果理直气壮地叉着腰。
真仪没理她,叹了口气,把那些被伊果扔乱的衣服重新捡回来。
她从背包最底下扯出一件最厚的灰色卫衣和一条同样旧的黑色运动裤,布料软塌塌的,没什么筋骨了。她把这套衣服铺在冰凉的榻榻米上,尽量铺得平整一些,权当是个简易的床铺。
又把那空瘪下去的背包拍了拍灰,折了折,弄成一个勉强能算是枕头的样子,扔在那堆衣服旁边。
“就睡这?”
伊果飞下来,用脚尖嫌弃地戳了戳那件当褥子的卫衣。
“硬邦邦的,下面就是地板,硌死人了!连层像样的铺盖都没有?”
“将就睡。等有钱了再买。”
“将就?这怎么能将就!”
伊果在她耳边嗡嗡地飞。
“睡眠质量关乎本大人的美容养颜!关乎神格稳定!不行,绝对不行!你得给本大人找个像样的窝!要软的!暖和的!漂亮的!”
她越说越激动,开始绕着真仪的脑袋转圈,金色的长发和翅膀带起细微的风,刮得真仪脸颊痒痒的。
“要那种……那种蓬松柔软的羽绒窝!或者铺满丝绸和花瓣的摇篮!最次也得是个干净舒适的软垫子!听见没有小真真!本大人命令你立刻,马上给本大人置办!”
真仪被她吵得脑仁疼,感觉刚才洗冷水澡压下去的火气又冒上来了。
她猛地一挥手,想把这只吵闹的“金色蚊子”赶开。
“你吵锤锤!再吵睡大街去!”
“你敢!”
伊果灵活地躲开,飞得更高,居高临下地指着真仪。
“你丢啊!你丢了本大人,看谁以后陪你说话!看你一个人在这破屋子里闷不死!哼!”
真仪瞪着她,胸口起伏了一下,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跟这家伙吵下去根本没完没了,而且她确实也累得不想动了。
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视线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扫了一圈,最后定格在阳台门边——
那里堆着几个之前房客留下的空纸箱,压得扁扁的,上面还印着“三洋电机”的字样。
她走过去,从里面抽出一个看起来还算干净,大小也合适的硬纸盒,大概以前是装什么电饭煲之类的。
她拿着纸盒走回来,三两下折好,砰地一声放在榻榻米上,正落在她刚铺好的“床”旁边。
“喏。”
她没好气地冲着伊果扬了扬下巴。
“你的窝。”
伊果飞过来,绕着那个光秃秃的方盒子飞了两圈,小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难以置信,最后出离愤怒。
“这!这破纸盒子?!你让尊贵无比,至高无上的本大人睡这玩意儿?!”
她的声音尖得快要刺破玻璃了。
“细川真仪,你脑子是不是被冷水浇坏了?!这是给流浪猫睡的,不是装神的!”
“爱睡不睡。”
真仪懒得再跟她废话,转身关掉大灯。她和衣躺在那堆旧衣服上,缩成一团,试图保存一点体温。累了一天,她现在只想让耳朵清静点。
“你!”
伊果气得在空中直跺脚,浑身的光晕闪烁不定,把昏暗的房间照得一亮一亮的。
她看着真仪真的是一副打算不管她死活的样子,又看看那个丑陋的纸盒子,小脸一垮,开始干嚎起来:
“呜……欺负神了!没良心的小真真!虐待狂!本大人怎么摊上你这种人呀……命苦啊……”
她一边假哭,一边却还是晃晃悠悠地降落在了纸盒边缘。她扒着纸板,探头往里看了看,又嫌弃地缩回来,用手扇着风。
“哼,脏死了!灰好多!咳咳!这味道……一股子陈垃圾味!”
真仪闻言只是翻了个身,背对着她,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那假哭声渐渐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窸窸窣窣的响动,还有伊果小声的,嘟嘟囔囔的抱怨。
“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还得本大人自己动手……岂有此理……凡人就是靠不住……”
然后是更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伊果在使劲儿时发出的“嗯嗯……啊啊……哈!”的用力声。
真仪皱了下眉,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偷偷瞄过去。
那个原本普普通通的硬纸盒正从内部透出微弱的金芒,一闪一闪的,就像里面藏了萤火虫。
伊果整个人都钻进了纸盒里,只能看到她那金色的长发发梢露在外面,时不时晃动一下,显然正在里面忙活着什么大工程。
真仪看了一会儿,实在搞不懂这家伙又在发什么神经,但好歹是安静下来了。
一天的疲惫和初到陌生之地的茫然感如同潮水般涌上来,眼皮沉重得打架。
就在她快要彻底睡着的时候,纸盒子里的动静终于停了。
“呼……差不多……勉强能看了……哼,真是便宜你这破地方了……”
伊果满意的声音传来。
真仪被这声音又弄得清醒了一点。她终究是没忍住那点该死的好奇心。她撑起一点身子,探过头,把盒子掀起一边盖板,朝里看去。
这一看,让她愣住了。
纸盒从外面看还是那个破纸盒,印着褪色的家电广告。
但从内部看,已经完全变了样。
原本粗糙的瓦楞纸内壁,此刻仿佛被覆盖上了一层细腻光滑、散发着珍珠般柔和光泽的材质,上面还用更亮的金线勾勒出繁复而精美的藤蔓花纹。
盒底铺着一层看起来就无比蓬松柔软的白色垫子,像是一朵云彩被塞了进去。正中间放着一个流光溢彩的金色靠枕。
角落里的光芒最盛,似乎镶嵌着几颗细小的……碎玻璃?不,在此刻的光线下,那璀璨的折射光芒,竟真像是微缩的钻石和红宝石。头顶还悬挂着一个正在发光的“水晶吊灯”。
整个空间被营造得称得上奢华,这简直是一个为拇指姑娘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
“喂!谁让你偷看的!”
伊果正叉着腰,站在那柔软的云朵垫子上,满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抬头看见真仪那张放大的、惊讶的脸出现在“天花板”缺口处,立刻飞起来试图挡住她的视线,小脸涨得通红。
“还没完全弄好呢!不许看!这是私人领地!本大人的寝宫是你能随便看的吗!转过去!快转过去!我要收门票了!”
真仪看着眼前这个在破纸盒里凭空造出的华丽小窝,又看看伊果那副明明很得意却非要装作气急败坏的模样,一时之间竟然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
“……整得花里胡哨的。”
她嘟囔了一句。
“睡觉。”
她也懒得再理会伊果的大呼小叫,重新重重地躺回自己那硬邦邦的“床”上,拉过那件旧卫衣的一角,胡乱盖在身上。
冰冷的榻榻米硌着她的背,空荡的胃里虽然有了点东西,但那种不踏实的感觉依然存在。
明天……到底该怎么办呢?
思绪乱糟糟的,像是一团解不开的麻绳。
但身体的疲惫最终战胜了一切。
伊果似乎还在那个华丽的纸盒宫殿里嘀嘀咕咕地抗议着什么,声音却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终融入了窗外那座巨大城市低沉的呼吸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