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站在门内,我站在门外。笑眯眯的他穿着身短衣长裤,花白的头发,满面的皱纹,像是外环村中的老人。他见了我,便放下手中的活,笑起来了,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身子挺得直愣,哪有半分老年人应有的气色。
老人面色红润,张大了眼,喜气极了:“娃子,回来啦?”迈开步子,伸开双臂,就要接过我背上的包袱。我赶忙伸出了手,搀过老人,一并向屋内走去,再将包袱放在桌上,哭诉道:“先生!我有愧于您啊!”说罢,就要弯下身子,可身子还没着地,便被老人搀扶起来。老人拭去我的泪水,笑着问道:“你做错了什么吗?老头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俩围坐在炉边。老人沏上热茶,斟满两碗,看着碗中茶水,愣神许久,似在忆想过去。过了半晌,老人笑着问道:“今个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你想听吗?”我轻轻点头,捧起茶碗,看着水中茶末。
老人小口抿着茶水,开始娓娓道来:“以前啊,这里还是个村子,一个很小的村子。后来啊,围了墙,是要发展的,来得人多了也就成了城。外来的人向里面挤破了脑袋,他们是挑担子的,也就停不下脚步。这是祖辈们讲给我听的。
“环南的边陲小城并不大,也就没人给起个名。来的人大多是盼望的, 城也就有了个‘盼’字。盼望的东西很多,但最多的还是熟悉的,饱腹暖身的铜币,朝思暮想的亲人,但总归还是盼着一个家,城这又带了个‘乡’字。两个字合起来呀,便成了‘盼乡’,也就是这城的名了。
“城里来了六个青年,精明的叫瘦猴,蛮横的叫痞子,呆傻的叫麻子,耐劳的叫憨子,精猛的叫愣子,领头的是个死脑筋的痴儿。痞子想着要身强力壮才能防身,愣子想着要武艺高强才能仗义,两人便一同去习了武。瘦猴家中穷困,自是将钱财看得极重,脑子又出奇得灵光。便买了别家的货,卖给这家的人,就这么跑起了商。憨子没多想,就这么挑起了担子,平日蹲在街角接些生意。麻子打小喜爱听他人说书,平日跟着憨子挑担,闲下来就跑去茶摊听书。可痴儿自视甚高,跑去城中私塾,就嚷嚷着要念书,赶出一次便要换上一家。
“也不知跑了几个年头,换了几家私塾,去了几家书院,却是没有一家愿收他的。痴儿站在书院外叫骂:‘就因我这副模样,你们便看不上我,你们这些自视甚高的人怎能称得上先生!若是叫我读上几年书,怎会不如你们?’院内走出个老先生,一身黑衫,笑着问道:‘小娃娃,他们看不上你,可你却将自己看得不低呀。若是按你所说,叫你读上几年书,你可是能登上那座山?’痴儿咽了口唾沫,壮壮胆子,指着那山尖:‘能!’
“老先生笑得愈发开怀:‘你就这么指着岩山?不怕山上的神怪罪?’痴儿涨红了脸:‘爹娘说过……神深爱着众人,这才有了岩山,自是不会怪罪众人。’老先生拍拍痴儿的脑袋,指着头上的牌匾:‘娃娃,这门上挂着的牌匾刻了什么?’痴儿望着牌匾,口中嘟囔着,却说不出是个什么字。老先生哈哈大笑:‘上面刻着的,正是书院的名,叫做民生书院,也是你今后要待的地方。出身众人,托举梦想,心怀无惧而先行者,便是先生。你可要谨记在心。’”
我愣愣地捧着茶碗,却是一口没喝。老人为我换上热茶,问道:“还记得你来时说了什么吗?”茶水映出我的模样,我便骗不了自己:“先生不怕恶人、无惧欺压,所以我要成为先生,让家人不再遭受苦难……”老人笑了:“你可知先生为何无惧?”我摇摇头:“我不知道……”老人只是笑着,什么也没说。
老人看看时间,掏出块布,包上酒坛:“山石,陪我去见见几个老兄弟,今个还有宴席哪。”我伸手想要接过老人的包袱,却被他用手拍开,只得跟在后面慢步走着。
先是去酒楼取了菜,随后便向着城外走去。愈是向外走,行人便愈少,直至再也见不到人。那是一片墓园,死气沉沉的,本就西斜的残阳显得更加阴沉。
老人坐在坟墓前,将酒菜摆了一地,笑着招呼着:“哥几个,都等着呢?今个可是喜庆日子。我这徒孙没忘啊,没忘了自己的‘心’长在哪!”老人抱起酒坛,大口喝着:“我这心呀,可算是放到肚子里了!这好酒好菜也给哥几个办上了,都敞开了吃啊。”
老人笑着、喊着,好似周遭坐满了宾客。大口喝着、吃着,却也停不下口中的话。老人的腰弯了,精神劲也散了,看着冷冰冰的石碑,打着酒嗝:“哥几个,我老了……我想你们了……我不想死在岩山下……”
老人瞅着我,傻傻笑着:“山石……扶我回去吧……”我背起老人,借着月光,向着店铺走去。老人迷迷糊糊嘟囔着:“山石……心怀无惧,便已是先生……做个自在的人……”
次日,老人起了个大早,拾掇着一包的行李。我打着哈欠,问道:“先生,是要回家了吗?”老人笑着回应:“我老了,是该回去了。”我向着老人躬身行礼:“恭送祖师!”老人托起我的手臂,拍拍我的脑袋,笑道:“山石,还记得我说了什么吗?你愿称我一声‘先生’,我便做你一时‘长辈’。我能卖掉你手中的担子,却卖不掉你肩上的担子,你长大了,是要扛起它了。宇文小子还在等你,可别让他们久等了。我走了……”说罢,老人背起包袱,便向着城中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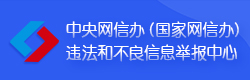


这个文笔好啊![[s-7]](https://resource.mfuns.net/image/sticker/s/7.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