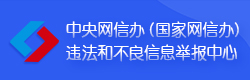前些日子外环闹了疫灾,毒死了秧苗,又病死了大片的人。我写了信,又寄了信,想着娃子能收到。可出了门的人却是没一个活着回来的,那封信应是没了下落。
我恳求师父将我的家人接来,待入了夜,他便出门求人去了。直到天边亮白,弄得身体狼狈,这才回了书院。他吃力挪动步子,膝盖沾着尘土,阴沉得将要流泪,说了句“没法子”,哀叹着进屋休息去了。
贾师兄走了,门老爷子便没了伴,整日坐在门口,望着来往行人,像是丢了魂。师父和先生是来劝过的,师娘也每日送来饭菜,小宇文想尽了办法惹他开心。
许是门老爷子也疯了,他觉得旁人都病了。他说这病比外环的疫灾更加可怕,是看不到的,父母传给孩子,先生传给学生,长者传给后生。
他说这病害得人无法相知,便要写一本书,要记下这害人的病,又要写一个人,一个怜爱他人的人。可他不知道什么是相知,也不知道什么是怜爱,只是心有所感,觉得自心中而发,传遍四肢百骸,于口中脱出的那股温暖,便是他所求的。
他话愈发少了,又拿起了纸笔,翻看着书本,让小宇文教他念字。他并非不知先生学识渊博,只是他们病得太深,就连口中的话都被框住了。他想要自救,便只得向跳脱的孩童寻求。
他觉得是自己的眼睛浑了,只看得到病将众人隔开,却怎么也看不清病是什么。他想着病总得有个症,或头顶的脓疮,或身上的肿块。便打定主意,下了土坡,进了县城,用糖果向孩童换来答案。可孩童吃了糖,哈哈笑着,怎么也看不出病在哪里,只有手中的风车“呼呼”转着。
他觉得是孩童的眼睛太亮,就像夜里的灯火,吓得黑暗与疾病不敢靠近。如此便忆想自己的童年,想要找回几分孩时的样子。可回忆中满是悔恨,只有先生教导他去爱众人。只是他不曾问过如何去爱,如今也没法去问了。
他这么忆想着,许是太过久远,只忆起他作为孩童的最后一眼。坐在去往中环的车上,望着破旧的庙宇。他向同行的长者询问,长者说那是素衣的庙,是深爱着众生的神明。庙外站着他爹,以及他的兄长,还有那陌生的嫂子。
他哭了,哭得没有声息,却震得心肝发颤。不知为了谁,又为了什么,只是悲伤,便想要哭泣。他闭了眼,向后倚靠,许是病了,许是倦了,连笔都提不起了。小宇文轻轻合上书,又为他盖上被子,放轻脚步离去了。
他去买了不少粮食,装满了车子,又来与师父道别,想要去外环救灾,顺带着回家看看。师父和我一同目送他离去,城门外堆满了死尸,驾车离去的他便是唯一的活人。
过了些时日,孩童们欢叫着追逐,说着什么幻光,可一旁的长者却什么都没看到。外环的疫灾也随着幻光一并散去了,据说是素衣庙中的石胎生了灵智,就这么救了众人。还有人说那日庙中走出的是个白衣白发白瞳的少年,是那位少年救了众人的命。